分享
“崖丽娟诗访谈”:能激发我的肯定是好诗---陈东东答崖丽娟十问
2022-03-01 12:00 阅读量:7k+
华人号:南方诗歌
陈东东:能激发我的肯定是好诗
----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
您是第三代著名诗人代表之一,从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持续写作四十年,一直活跃在当代诗坛现场,您属于那种可以一直持续写作的诗人,长期写作中您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欲望?
陈东东:
这真不好答——这就跟要我谈一下怎么到现在还活着一样简单,也一样麻烦。那属于共同经验的方面不必说,属于特殊经历的方面,说了对别人又没什么用,用不上。而且,我的创作欲望实际上不旺盛,也没有有意识去保持,没有保持的方法可以讲。
我想起去年有一本对十个诗人的访谈录结集出版,其中也有我参与的一篇问答,提问者加在前面的小引里说我“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也是跟实际情况颇有些出入。其实我“始终”都不会勉强自己,更不摆那种“坚持”的姿势……至于贴我“知识分子写作”的标签,跟贴在这里的“第三代诗人代表”的标签,给我的感觉也差不多——前几天我还在和敬文东的一组问答里说起:“我1981年开始写诗,正读大学一年级,我的出发点跟1982年在西南师范大学桃园打出‘第三代’旗号的那些大学生诗人几乎是一样的,这是我没有不同意被归入‘第三代诗人’的原因。我又觉得这个名头于我不适,那是因为关于‘第三代诗人’,后来有许多讲究,有些显然应该把我排除在外了……”
崖丽娟:
您的诗歌备受赞誉,一直为人称道,2019年获得“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2018年、2019年您都分别出版了两本诗集,这四部诗集的出版无疑对当代诗歌写作具有某种示范作用,《海神的一夜》是您写作多年的短诗选集,请问您最满意的有哪几首?《流水》是您的长诗,创作长诗和短诗各有什么体会?是否可以结合自己的创作谈谈什么是好诗?
陈东东:
我不在这里专门推荐自己的某几首诗,大概想要让人去读我诗集里的每一首诗。另外我一直都在改来改去自己的诗,很可能并非真在往好的方向改,很可能改还不如不改,但这么去改,一定表示我一直不太满意自己的诗。所以我不推荐,主要因为并不能确定有我写得最满意的诗。关于我的长诗和短诗,我也有差不多的感想,没有觉得一方面比另一方面更满意或稍逊,在我的写作历程里,它们两样都重要,都有必要。
关于长诗和短诗,我先前对它们有过谈论,在被访问时,在零星的笔记里。爱伦·坡《诗的原理》一文“认为长诗并不存在”,“坚持认为‘长诗’这种说法绝对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用语。”他的理由:“诗之所以是诗,仅仅是因为它可在启迪心灵的同时对其施予刺激。……但由于心理上的必然,所有刺激都很短暂。所以这种使诗成其为诗的刺激在任何鸿篇巨制中都不可能持久。”那么在他看来长诗其实是拖长了的短诗……依此当然可以说,他以为的这般“长诗”并不成立。然而长诗一向就存在并且成立,从古到今的例子可以随口说出一长串来——要之,它们并不是爱伦·坡指认的被拖长的短诗,而是不同于短诗的另一种诗,应该说长诗跟短诗属于不同的两样文体。短诗也许更侧重诗歌语言施予的刺激,长诗的力量,则更多系于它的结构装置、架设筑造。短诗更纯粹于诗,长诗总是愿意跟相对于诗的诸如神话、历史、故事、传奇、小说、戏剧甚至论文等等体式结合在一起。组诗也形成为它那种样式的一种长诗,就算把几首短诗并置在一起的组诗,其叠加和布局,也就会给出不同于分开阅读那几首短诗的新的张力。我曾比方说写短诗是跑步,写长诗则是在骑自行车,助以从诗歌之外借来的别的器械……你提到我的诗文本《流水》就是这样,从古琴曲《流水》借用不少,甚至语言方式也跟古琴文字谱有关联。有人曾打算将《流水》改编成现代舞,我想改成清唱剧或皮影戏也都会很有看头。又比如我1994年的长诗《喜剧》,它情节和章节的场景化安排,适合做成一出音乐剧,也的确有人跟我聊过这方面的设想。
关于什么是好诗,最好不要有统一标准,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统一标准,答案必然因人而异。我觉得能激发我的肯定是好诗——包括那些并非以文字写下的“好诗”。
崖丽娟:
诗歌语言精炼,语言技艺在您的诗中占据突出的地位。您认为语言的作用在诗歌中不仅仅是表达,更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臧棣曾说您的诗歌是“汉语的钻石”,钟鸣也认为,您“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但也经常听到读者抱怨有些现代诗晦涩难懂,您如何归纳自己的诗歌语言特色?通过语言媒介,您如何处理和安排词语从而让读者在审美中感受到诗艺的力量和诗意的愉悦?
陈东东:
诗作将在读者那里引起什么样的反应,说到底是写作者自己对自己的写作之期待。我不止一次引用过苏珊·桑塔格那句话:“永远不要考虑读者,只考虑文学”,我觉得这真是想得明白也讲得明白——写作者要考虑的是文学对你的写作之期待:你正在写作的那件作品,期待着被你前所未有地诞生出来——而且,实际上,这才最大限度地考虑了读者。所以,大概,我很少去想“如何通过语言媒介让读者”怎样怎样这种事情……我忘了我的写作初衷和动机里是否有过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性,也忘了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朝这方面做过什么动作——想不起来了说明我当时没有故意或刻意于此,至少留不下故意或刻意于此的印象了……而回头拿自己写下的那些诗做这个题目的分析研究,肯定尴尬荒唐……那根本不应该是我的事情,不应该由我自己来“再创作”。另外“归纳自己的诗歌语言特色”,我同样做不了——还是不归纳,一首首去写去让人读就好。
崖丽娟:
四十年来,您和当代诗坛很多重要诗人保持深厚的友谊,写了很多唱和诗,可见您是一位特别珍视友情的人,我国古代文人一直有互赠诗文的传统,对此怎么看?2020年、2021年您先后编著出版《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显然也是对故友的怀念,请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编辑情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您办民刊有声有色、参与诗歌运动风生水起,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谈谈您的诗歌往事以及与诗人之间的交往。
陈东东:
被问到“怎么看”,我就差点儿不知道怎么看了……我一向将那些唱和诗(古人的今人的)跟别的诗歌同样看,同样读,当然也会特别留意这种诗怎样处理友情、人情、人际关系间的应酬之类,蛮有意思的。我自己写了这样的诗,估计也会被那样看,那样读,比如你就讲了一种看法。
海子和骆一禾分别于1989年的3月底和5月底离世,第二年我编印过《倾向》诗刊的“海子骆一禾纪念专辑”,三十年后受委托编了一本《骆一禾诗选》,再就是挺厚的两本书,《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和《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这中间碰到很多困难,很多阻碍,很多曲折,无奈和妥协,书的内容方面留有不少遗憾,就不一样样细说了,反正算是做了点事情。还有其他“诗歌往事以及与诗人之间的交往”的情况介绍,会很啰嗦,按下不表。
至于你说的“有声有色”和“风生水起”,我觉得这两个成语并不适合我。真要能够“有声有色”,用北方土话说,“那敢情!”;可要是“风生水起”了,我想我会看不起自己——在这么个时代,这么个国度,这么不堪的世道,你还弄得“风声水起”的,像话嘛?我会告诉自己离“风生水起”尽量远一点。传说有个外国诗人很严肃地认为自己的读者超过三百就表示他的诗太俗不可耐了,这听上去也难免另一种市侩;不过,“风生水起”,那敢情太可疑,太同流合污了。
崖丽娟: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您认为现在还存在这个壁垒吗?您对现代诗坛现状如何评价?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对现代诗发展有什么样的预判?
陈东东:
这些我都不太关心,有些对于我算是假问题或假话题,比如你说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还有什么“壁垒”,应该是弄媒体的,搞评论的,做研究的,还有教授们混诗歌饭会比较有兴趣吧。我知道也有诗人在这方面浑水摸鱼,那倒并无不妥,诗人去到自己的诗歌场域诗歌话题(哪怕无聊甚至伪劣)怎么胡说怎么玩闹都不为过,不妨观赏。但我搞不来这些,的确不喜欢这些。
对现代诗的评价,找它的问题,预判它的发展走势,如何才理想,我更是缺一套炒股预测专家那样的说辞。这基本上是为一连串全国性或国际性诗歌研讨会准备的议题,我最烦最怕那样的要为此发言的会,真到了场面上就只好耍赖,无语……我愿意说的是我还会继续写,写成什么样要等写出来看。
崖丽娟:
2021年有一部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大热,沪语小说也有优秀的作品,似乎听闻您倡导沪语诗歌创作?您最近写了很多地名诗,从国内到国外的地名都有,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创作计划吗?
陈东东:
你“似乎听闻”的估计照四川人说法就是“不存在~~”——我并未“倡导”。我偶尔试着用上海话写诗,写一些“沪俳”,照上海人说法只是“写写看”,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成品。另外我在写一系列我称之为“地方诗”的诗,计划完成一本叫《地方诗》的诗集。
崖丽娟:
您轮流在深圳和上海两地居住,异地流动的经验对创作视角有影响吗?您认为深圳和上海是有“诗意”的城市吗?“诗意”对一座城市、对个人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上海诗人和广东诗人(深圳诗人)群体的地域特点有什么深切体会?
陈东东:
前两问,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什么样的影响”却难理清,在此应可以借用苏东坡那句“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近十年写的诗,里面会有些“影响”的影子吧——肯定有的。而“上海诗人和深圳或者广东诗人群体的写作地域特点”,像个比较研究的课题,我没有特别关心过,真要谈的话需要先收集足够的资料,并且,尽管我对两边都有接触都有经历,但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反倒会弄不明白。
崖丽娟:
您的诗蕴藏丰富的哲理,怎么看待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如何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大学毕业后您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一段时间,具体什么原因促使您离职专事写作?成为一名诗人是您安身立命之本吗?
陈东东:
哲学方面,我所知甚少,可以说并无哲学修养,哲学训练。以我浅陋的看待,哲学大概是一门学问,一些理论,也会拿诗人和诗来理论,来做哲学的学问。诗呢,关涉人的方方面面,而且跟语言脱不了关系,那么它免不了去处理哲学方面的材料。我记得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就是用诗体写成的,老子庄子的著作,也不妨读作诗。诗和哲学,至少有这样的关系吧。
说到诗跟现实的关系,好像很复杂,反正已经有很多议论,七嘴八舌的,我也插个嘴学个舌——我想说诗刚好是一种现实,当一首诗问世,它也就成了一个现实;所谓“处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大概就是将呈现为语言的世事万物之类的现实介入诗,接纳进诗,成为诗,以之介入现实,接纳进现实,成为新现实。
我越来越同意“诗就是生活”这样的说法,你问的诗对我的意味和是否安身立命之本,都能从这个说法里找到答案。
我大学毕业后上了十三年班,后来离职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讨厌开会,感觉开那种会很妨碍写东西。
崖丽娟:
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是双轮驱动,我们发现,很多好诗人也是很好的批评家,反之,很多好的批评家的诗写得也很好。最近看到您解读上海师范大学同学陆忆敏的三首代表作《Sylvia Plath》《对了,吉特力治》《美国妇女杂志》确实大受启发,有人认为,越来越多的诗人写作诗歌评论是因为对诗歌批评的不满足,您怎么看?
陈东东:
你说的我大致同意,问我“怎么看”的话,我差不多也这么看。不过我在文稿里只是写一些自己读诗的感想体会,算不上批评的。我也没想过要去做批评,而是从一个诗人返回普通的诗歌读者,去看待去赞赏诗歌。
崖丽娟:
诗歌作为一门特殊的综合艺术,在诗歌创作中,灵感、激情、经验、知识、想象……在诗歌创作中,您认为哪一个因素更重要?您关注年轻诗人的写作吗?作为当代诗歌最成熟的诗人之一,您对他们的创作有什么建议?
陈东东:
当然,那些都很重要,都最重要。既然诗歌关乎世事万物,那就没有一样对诗的生产不重要,不最重要。
另外,当然,我读年轻诗人的诗,在我自己还不是诗人时就已经在读,在我自己还是个年轻诗人时就读得更多,一直读到现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仍然没多么两样……我觉得自己远未达到那所谓的“成熟”——“最成熟”(然后腐烂)更是让我害怕——很可能我有意无意地在避免和拖延我的“成熟”,宁愿生涩然而新鲜……这句话或可以拿来跟我的年轻同道共勉。
(2022年2月)

附:陈东东诗作三首
第二圈
这样,从第一圈我降至第二圈
较为缩紧的圜围,却容纳着
更多引起号哭的痛苦的方面
不过仍有时间为证,还能踏歌
深嗅更为悠久的恶之花
甚至彻底,甚至击穿了
地狱之心,跌进跃出,去熔化
装束起精神的押韵的链条
上登水晶天,更接近抵达
最后的幻象里最后的见教
即将背弃此生的誓约
以及自由意志的飞鸟
这样,第二圈,未必无月
照临雪原
翅影拂掠
(2021.10.10)
无解理
每当此刻,托起水晶球
让一束平射的黄昏之光
透过西窗刺入
将虚空抽象为抽象的虚空
天象于是为之转折
如那束光,并未受阻
却折转灵视
升起星夜坠落了词
室内剧里,有一个相反的
此刻逆行,水晶球迎向
透明对面刺入的光
一无充注也充注着一切
风,正吹,吹弯世界意志和
照耀。未卜恰是寻常的运程
每当此景,裂碎水晶球
没有谁会去理解无解理
(2011.10.10)
[简注]
[1-2行]参西川《唐诗的读法》:“杜甫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也就是个二流诗人。”
[4-5行]参《红楼梦》第五回:“安禄山掷伤太真乳的木瓜”。
[6-7行]参杜甫《丽人行》《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春望》。
[7-8行]参杜牧《阿房宫赋》,赵翼《题遗山诗》。
[13-16行]参李白《早发白帝城》《子夜吴歌·秋歌》,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杜甫《梦李白》《饮中八仙歌》。
[17-19行]参李白《清平调》,2012年9月西安“U型锁”事件,2022年1月中国防疫政策及西安社会新闻。
[18、19、26行]西安话“你”发音如“逆”。
[25行]参贾平凹答《北京青年报》:“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27行]参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
陈东东 出生于上海,现居深圳和上海。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近年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诗文本《流水》(2018)、诗集《海神的一夜》(2018)、《组诗·长诗》(2019)、《陈东东的诗》(2019)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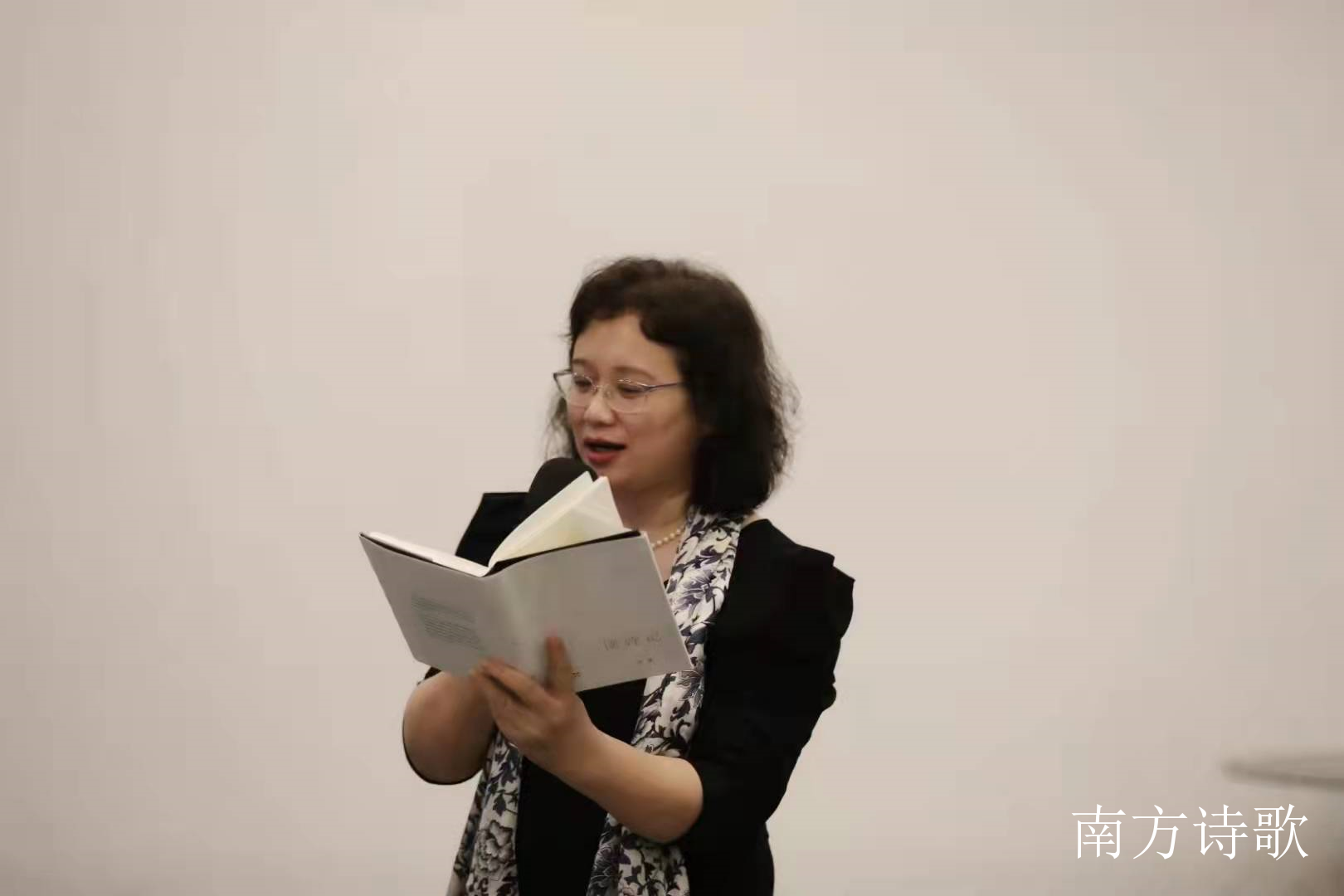
崖丽娟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研室主任、《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写诗,兼诗歌批评,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并有诗歌获奖。

2021年《南方诗歌》总目录
2022《南方诗歌》01月总目录
西渡:到南方去
尚仲敏:暗器高手
李啸洋:一瓣海棠
易杉:灵魂先生
“高山流水”黎二愣论崔体诗:自在与单纯的至简诗兴
楼河:樱花开放的时节人类需要悲伤的救济
铁链下的伤痕(选辑)
铁链下的伤痕(2)
铁链下的伤痕(3)
铁链下的伤痕(4)
铁链下的伤痕(5)
弹片撕裂天空
周薇:一次非理性的科学分裂实验
“崖丽娟诗访谈”:与石为邻---哑石答崖丽娟十问
远岛:第三只眼睛
庞培:马在黑夜里的样子
宫辉:你好,太平洋,这是我!
“90度诗点”张媛媛:诗意何以安抚乡愁---品读沈苇的诗
”他山诗石“““高兴译作:只用了片刻,我就成为你的篝火
沈荣均:春天来临之前
寿光晓:绿墙
顔梅玖:寂静的力量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崖丽娟诗访谈”:能激发我的肯定是好诗---陈东东答崖丽娟十问》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中国大陆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免责申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举报收藏点赞
评论
(0条)

您需要登录后才能评论,点击此处进行登录。
登录后评论
- 侨务
- 中国
- 国际
- 出国
- 财经
- 文化
④“四下基层”走访侨界困难群众|省侨联外联部赴儋州、临高、昌江走访慰问③“四下基层”走访侨界困难群众|梁谋赴东方开展专题调研中方就习近平将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答记者问|3分钟头条新闻(2025.5.4)胡允键:意大利侨二代的担当与突围——一个人、一代人与两个世界之间的连接带路东南亚|文明互鉴 粤韵生花:“粤韵杯”走进东南亚,开创华媒跨国协同传播新探索侨!我们就是这Young的青年千行百业志愿行 渝侨大爱暖人心—渝侨志愿服务队关于开展2025年“千侨助千家”活动倡议书5名中国公民在美国交通事故中遇难 | 3分钟头条新闻(2025.5.3)文博日历丨极简“宋式”穿搭 假期出游这么穿超出片
下载华人头条

关于我们
© 2022 华人头条
服务热线 : 0591-83771172
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直播备案号 闽ILS备201708250005
举报热线:0591-83771172
举报邮箱:hrtt@52hrtt.com
免责声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