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潘维:灵魂为什么举杯
2022-01-29 00:00 阅读量:9k+
华人号:南方诗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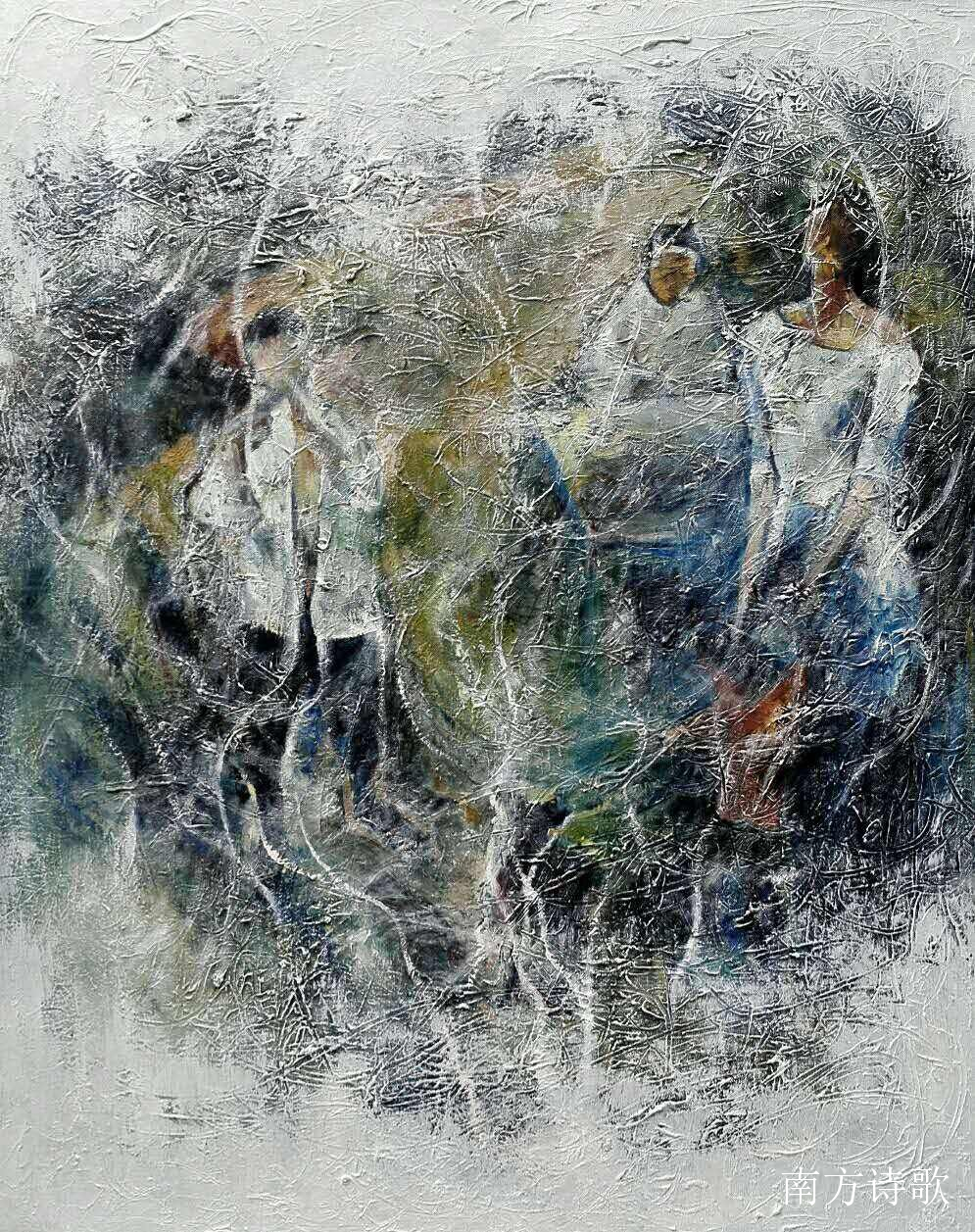
疫时日记
疫时,他用闲置已久的孤独,
自我隔离在郊外的连绵细雨里;
秒针滴答,似施了有机肥的农妇,
匆促细致地收拾碗筷;
多处水洼,那些碎银,闪烁着,
它们想用暮色抓住日子的衣襟,
但微风一吹,失败了。
一个外省青年,
狮子与宝石的信徒,
他不在意自己逃避了国家压强,
也不在意小人物的道德,这种善良,
对叽叽喳喳的邻里关系而言,
并没有什么豁免权。
如果,此刻,一旁的野花丛打开蜂箱,
上万只蜜蜂的嗡嗡声拧成麻绳,
如烟缕穿过牛鼻,
而牛粪正冒着泥泞的热气;
如果,此刻,地平线撞响城楼上的钟,
一种壮丽的熟美笼罩江南丘陵,
屋顶呈现冬至时所酿黄酒的琥珀色;
他想对穷人们说,
你们的果园,光秃秃的枝丫上,
笑和哭已果实累累。
2020年春
苦春
一
揭开雨水的伤筋膏药,
白墙上,仍爬动着蜈蚣老年的冷,
那种被冷漠消毒过的冷。
早晨湿漉漉的鼻尖,
嗅着萌芽:复苏的死亡胚胎。
野蜂的引擎停息在忧郁里:
解冻的瓦片,兔眼里的迷途,
本地有机小青菜,
除了这些可靠的寂寞,
到处是无法治愈的愚蠢。
天空灰暗,溃疡般显露压迫者的威势;
绿像一根碎石嶙峋的皮鞭,
抽打着流向树梢的水流。
二
今年苦春,一切脚步
都被瘟疫贴了封条,
电影院的坐椅找不到半张股票,
空荡荡的人间冒出
没有悼词、没有统计数字的烟。
每天,我听见一面受诅咒的锣,
又敲碎了家园的一部分。
我的视网膜不忍紧紧抓住那朵
穿越浑浊的小雏菊,
如淡黄的铁轨用风的灵魂,
运来了援军:泥土的重量——大地的钝。
多少辈子了,萤火虫一茬茬地收割牛鬼蛇神,
灰烬一遍遍点燃光阴,
可我们仍需用肩膀的承担
去哺乳自由;仍需用穿白大褂的雪
去救赎人性;
仍需用芦笛去摧毁恶俗。
此时,寒气还在继续,
当眼睛戴上口罩,夜就会降临;
当驼背挺直,真相便会隆起躺倒的山脉。
2020年春
挽歌
雪翻动树叶的银币,
我想起,
哪个少女不曾做过眼泪的盐贩子,
哪枚小鲜肉不是开门的钥匙,
有几个家庭不在税收和人情之间奔忙;
当苕溪里运送煤炭的船只,
颠簸着疲惫,随白鹭的鸣叫,
没入枯黄的芦苇丛;
有皱纹的灵魂才会告诉你,
水是有鱼刺的,
悲伤更是一条流淌着生命的骨头。
当高原的白,
帕米尔全体山顶上的白,
那不动声色静止一切的白,
停下脚步,
为俗世默哀!
我也要求自己:
停下工作,
停下天空;
伸出手掌,
区分每一片液体虎皮的善与恶。
2020年春
莫干山民居通知
一
天黑了,
蔷薇花正在来的路上,
与女护士为伴。
夜班火车载着她们,
向着湖州的山水;
仿佛大事临头,
莫干山居图已换好干净的床单;
她们是可以供奉的神,
她们用药棉轻轻擦去许多伤痕;
无论她们在精疲力尽的一线,
还是在谦虚谨慎的后方,
她们的针筒从不撒谎。
二
“探花及第”的民居大厅,
杯子里的书香已沏了绿茶;
卸下行旅吧,
顺便在懒洋洋的时辰,
给小蝴蝶把把脉;
农家的耙耧可以聚拢全部的露珠;
竹笋的拱土之力,
可以为春光发电;
无论银杏树下的蕨宿还是萤火谷,
无论羽毛枕之梦,
还是突然袭来的食欲,
这儿的咳嗽是翠绿的鸟语,
这儿的菜单恋着味道。
2020年春
寂寞
没有人气、没有风筝的街道,
紧闭着洗衣房;
懵懂初醒的窗子,
掠过鸟雀的摄像头;
今年三月,
始皇帝又增添了几吨赞歌:
连绵不绝的长城终于防御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近。
活了这么久,
我终于活成了一只纸老虎:
反复被各种夹兽器所虐,
被低劣的色彩所舔。
我的寂寞,
像冰原上的冷板凳,
不仅感染了餐桌,
也感染了天下粮仓。
2020年春
信使
火柴湿了,无法点亮屋顶,
整片天空低垂着安魂曲的阴郁,
环城河排着队,缓慢地蜿蜒;
那时,我跟随小镇居民的身后
购买食品,我喜欢烧饼铺门前的电影海报,
黄泥烤炉伸出细碎的焦味小爪,
抓挠女演员的雀斑脸,
我的莫名兴奋,
像撒了一把充了鸡血的芝麻;
这种与生俱来的魔性,
中止于图书馆走廊:她,
穿着针织长衫,一股异乡气质
迎面匆匆而来;背影
隐约着柔化了的坚定。
后来,一个有很多酒吧,
水光把梦折叠成纸鹤的地方,
铺展了另外的床单:
为我,惊蛰的雷,波斯纹的恶之花,
坍塌的微笑——它们翻滚着;
但没有一只燕子是她。
我凝望着岁月,
作为多数人分享的特产,
早已失去了爱与性的滋味;
只是,每月,当骑自行车的邮递员
穿过永远尘土飞扬的市区,
从绿挎包里取出《信使》,
整整21年,她为我订阅的思想,
像舍利子,守护着大悲殿。
2020.3.20
浏河镇
无论日子被拆建了多少次,
浏河镇的寂静,
永远没被推翻过。
每一个属于菜市场
的早晨,
形似蚁蚕细嚼的桑叶;
仿佛可以看见一丝丝晶亮的突然
需要引爆;
在肉铺前抖动腰肢的主妇,
从罐子里取出咸和甜,
这种普通,产生的韧劲,
如木锤砸打石臼中的熟糯米:
柳风般折不断的
吴侬软语,弥散着。
无论隔壁的大都市如何高耸入云,
这儿的基座,
由淤泥、汽笛声,
和为河豚献身的勇士浇筑。
当船只入水的刹那,
白光涌现;
天妃宫的桃花
多么心疼——猫咪的叫春。
自从,
帝国最灵的童男童女,
起锚这块地理,
港务局海运就失去了淡季。
2020.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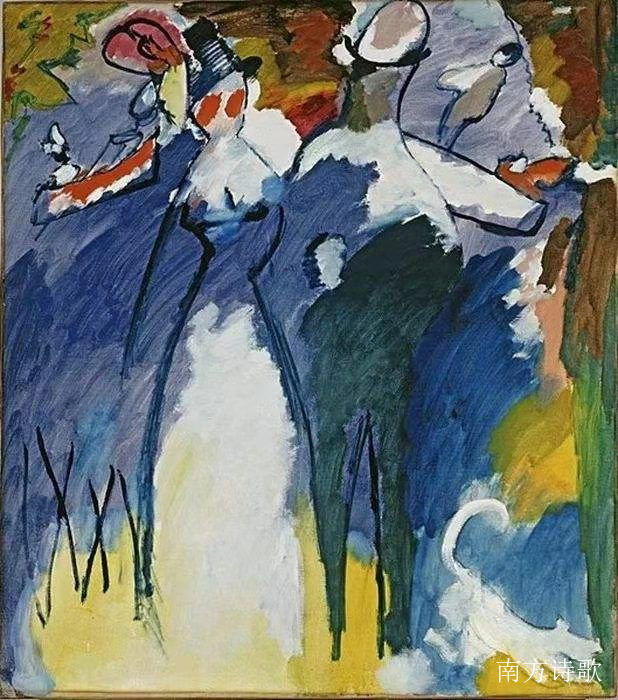
列车上的少女
——致竹君
一
十一月的猫爪,
沾了江南的阴冷;
雪,还没起床弹棉花;
神秘,似四季酒店半梦半醒。
那少女,发梢微卷,
随众多脚步汇入一列
密集的铁皮火车;
生的迷惘
不断疾行;
这种流逝,
随时可以伸出细雨的手掌,
轻轻一拍,
就把旧时泥泞打翻在地;
或者,
那裹挟着速度的玫瑰,
掠过平原、乡镇,
掠过《神曲》,
抵达:她的自我。
二
少女斜倚窗框,
似永恒的爱慕,
似一堵阻挡逆流的墙;
她用天然溢出的
现代气质,
反对农耕黑暗:
那浸猪笼的秩序。
各种粗糙、无聊,
无向度的沉默,
狼藉了整个车厢;
她,封闭在自身里;
她,阿佳妮17岁的美,
燃起一朵朵
不可亵玩的暗火,
沿微颤的铁轨,
深入
2013年冻僵的城,
被酒审判过的城。
三
很快,
她会到达这个
赴约的早晨:
几根枯柳倒垂楹联,
坟堆里的苏小小,
彻底死去。
当她用一把伞,
收拢或撑起
新的天,
那倦伏在屋顶上的水光,
闻到了时代,
被寒风烫伤的焦味;
她并不向往,
每一个黄昏,
都是朋友们预订的座椅;
她知道,
在某个尽头,
失败是告别,
西湖是再见。
2020.3.31
深秋的湖畔
一个适合哀悼的深秋,
树林打翻了颜料罐;果汁
正在婚姻路上,
压榨仅剩的几滴爱情;
黄昏,像羊绒围巾,
些许暖意,裹着下班女工,
渐渐地,她们变淡、灰暗;
我想,我曾用阿拉伯神灯
去探寻、去跪舔的美好,
并非这股俗世的疲惫,也并非
风铃在床单上凝结的褶皱。
此刻,我将凤凰牌自行车,
停靠在1997年的湖畔,
那尚未执行计划生育的鲤鱼
偶尔跃出水面(雨是水经常的出轨),
给空阔增加了几个带腥味的问号;
堤岸上,那些中式飞檐,
似乎有足够充沛的精液,翘起
辟邪的灵兽;它们吸纳了太多的俗气,
以至于,这片遗址,
在蛇妖与和尚大战之后迄今,
相比法相庄严的诵经声,
更倾向人性膏状的药香。
期望,或许有一天,
医院这座菜市场,
在拥挤中崩溃,
所有的疾病,随之被清空:
这种哈哈大笑的拥抱——
才是平凡者的终极,伟大的起点。
2020.4.3
猫病了
傍晚,蜗牛收回地表温度,
河豚鱼把带刺的皮盖在蔷薇的枝条上;
龙舟在树木里又长了一点汁液。
幸福确实有些慷慨,
将时间静止在绿里,
因为猫,是肉钟之谜。
那无辜的警觉,
分泌出褐色粘稠物,
像眼眶挨了忧郁一记闷拳。
可怜,猫病了,
以一个少女的身体,
卷缩着,永恒般无助,胶原蛋白流失。
她的每一阵咳嗽,
都穿透医学联盟福尔马林味的大厅;
肺页,沉入缺氧的水底。
没有疗效:厨房救生圈,
比莉·霍丽黛饱受魔法侵蚀的嗓音;
连话语也艾灸不了她的情绪。
她就是那即便近
也无限远、半透明的神:
一尊春,撒下药饵、阴之网。
2020.4.9
开封,地下的中国
中原的头顶悬着一条黄河,
飘忽如丝路,
凶险似利剑,
水夹泥沙冶炼着刚与柔。
在所有的古籍中,
它没有标点符号的堤坝,
如果说泛滥是文化的必然,
那么,当我进入开封,
停步在
为旅游业仿制的龙虎狗三头铡刀前,
我能想象,
倒影水面的铁塔抽搐、扭曲的
泪光,包含了多少暴虐。
每一次黄河决堤,
就把一座城从人间抹去,
几十万条生命铸造一层地狱。
在我脚下的土里,
有六座城,城与城垒叠;
六层死亡:一层层绝望与挣扎。
之前几十秒他们还鲜活在
最大的繁华,
清明上河图的实景里:
货物重压着午后,
酒旗云集了紧张和慵懒,
新娘的花轿抬高了拱桥的春色;
生锈的士兵梦见,
驼队运来异域的消息;
快乐,船只般在账簿上递增。
很快,受惊的马蹄
踢开城门,不设防的菊花,
随意践踏路面;
我想告诫的是,
自然的报复与人为的灾难之间,
横亘着一条底线:文明;
可事实无数次见证,
恶之手骨骼粗壮,
它们挥舞蛆虫般蠕动的汗滴,
扒开杂草丛生、浑浊庸俗的河堤,
放出吞噬爱与呼吸的绞索,
这只以人为食的恶手,
无不沾染了权力的狂怒,
和麻木的愚蠢:
从秦帝国的铁军到闯王的乌合之众,
相隔两千年,目的和操作技术
几乎完全孪生,
并且,毫无禁忌。
当徽宗的宫殿,
在滔滔汪洋中,
留下最后一瞥瑰丽,
屋脊上千百只飞舞的白鹤,
瞬间变成遮天蔽日的乌鸦;
富庶就这样通过暴力,
转换为饥馑;
肥沃疯涨着茅草,
记忆就这样被尸骨埋葬。
当日出日落的繁殖系统
又一次刷新大地;
慢慢地,鸡鸣在废墟上
搬运市声;雨,
洗去晚霞的血腥;
小吃的吆喝从老街传入巷尾,
只是口味略显急躁;
木匠们又开始用新木材
制作老式风俗;
然后,遗忘蔓延,
历史紧锁自己的嘴,
山水花鸟继续刺绣。
喧闹的鼓楼夜市,
溢出烧烤的啤酒泡沫,
这酣畅、尽兴的河南梆子,
让我不禁疑惑,
苦难该怎样沉醉?
灵魂为什么举杯?
我问那些财产,
我是不是盗墓者的同伙,
可我挖掘到的却是
地下的中国,它哭泣着。
2020.4.7
鲁迅回故乡
船尾的涟漪拖着月牙,
水声潺潺似有人抚摸铜钱,
严寒使摩擦系数增大;
那木桨,已失去初露纹理时的躁动,
呆板、僵硬:一条冰冻的白鱼。
狭小的船体,笼罩着黑篾篷:
微暗里,拱形的浮游生物
低矮穿梭;冷,
从缝隙向村落投掷薄冰,
和几丝耷拉的活气。
炊烟,缺少稻草喂养,
细小而无力;
田地,一副萧索影像;
两岸的山,呈现乌毡帽的轮廓;
随荒凉不断长高的墙,越来越模糊,
如变了质的乡音,
陷入重度沉默。
天底下的悲哀,
颤巍巍地摸索着老油灯;
很快,焰苗枯瘦了下去。
一如既往,豆腐切得方方正正,
岁月仿佛是官吏的小姨太;
咸亨酒店说着胡话,
像中年醉汉;各种熟悉的脸,
尽是从土里捡起来的陌生人。
2020.4.14
女理发师
简洁,但仍然是野兽派风格的室内,
镜子分泌出阴影、镀锌的温暖;
她抖动白围布,“啪啪”,性感掉落,
像万有引力承受了那一瞬伤心的决绝。
有时,当她穿过人群,落日般
一个回头,就把街道又红烧了一遍。
这似乎暗示了昨晚的某部电影,
挤进了这个肥皂味充塞的空间。
她的技艺如一支流行歌曲,
兼有长柄梳的专注及鹿齿剪的随意。
可以想象她平庸的日常:蓬乱的惺忪,
马桶的抽水声,粗俗所引起的某种坍塌;
偶尔,她把表情固定在失恋刻度,
那无非是对升降椅的一次踩踏。
当我起身,掸去领袖上的碎发,
湖边的城习惯性地绽露微笑,
白云飘着几片绿茶;搭扣轻微碰撞,
玻璃门闭合了我离去的虚空。
2020.4.18
谷雨
又一次听见泥泞的瓦片在窃窃私语,
在这座以它的庞大把我碾压成扁平状壁虎的
都市:果盘里盛满凉爽,
打开的抽屉散落着药片。
时至暮春,随处撒网的雨,
并没有捕捉到布谷鸟的啼叫,
出站口也没有迎来任何意义。
因此,一个循环的扣缓慢地滑行着。
如何才能解开这人与天之间的困境?
如何让刺穿云端的尖顶,
俯下资本的谦卑?
黄浦江就这样驱策着
外滩的花岗岩头脑,驱策它们
去吞噬血运旺盛的牛排。在这个幽暗区域,
大多数是被从事阶级分化的陨石所砸中的人。
又一次快递员投入茫茫无穷:
那封信,用梧桐路的胶带
包裹着;而我的套鞋
响彻了拔节声,仿佛脚步就是受滋润的禾苗。
而那些紧闭耳膜的窗户,
强化了死者的作用。
2020.4.20
光线和盐
那上楼的脚步发了芽,
一种犹疑拖着泥土;
那托盘端来的早晨,也不快乐。
瞧,蚂蚁糜集起那么多阴郁,
无意义犯了有刺的罪,
天幕上布满了指甲痕。
(也许,我并不适合被腌在酱缸里。)
作为草莓与丝绸的后裔,
我想做太湖的白鱼。
用冒烟的银鳞去纺织
水网:当经纬密布的呼吸
抬高屋顶;
老城区听见,
青一块紫一块的鼓点像蒙受的苦难,
落在牛皮上,
它背负过暴风雨,
也为我的灵魂剧院:记忆,
驮来了光线和盐。
2020.4.25

潘维,1964年出生,浙江湖州人,多年生活杭州、上海。做过电影放映员、编辑、纪录片制片人、大学教授等工作。获柔刚诗歌奖、天问诗人奖、两岸诗会首届桂冠诗人奖、《诗刊》年度诗人奖,闻一多诗歌奖等十余奖项。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著有诗集《不设防的孤寂》、《潘维诗选》、《水的事情》等。进入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国家一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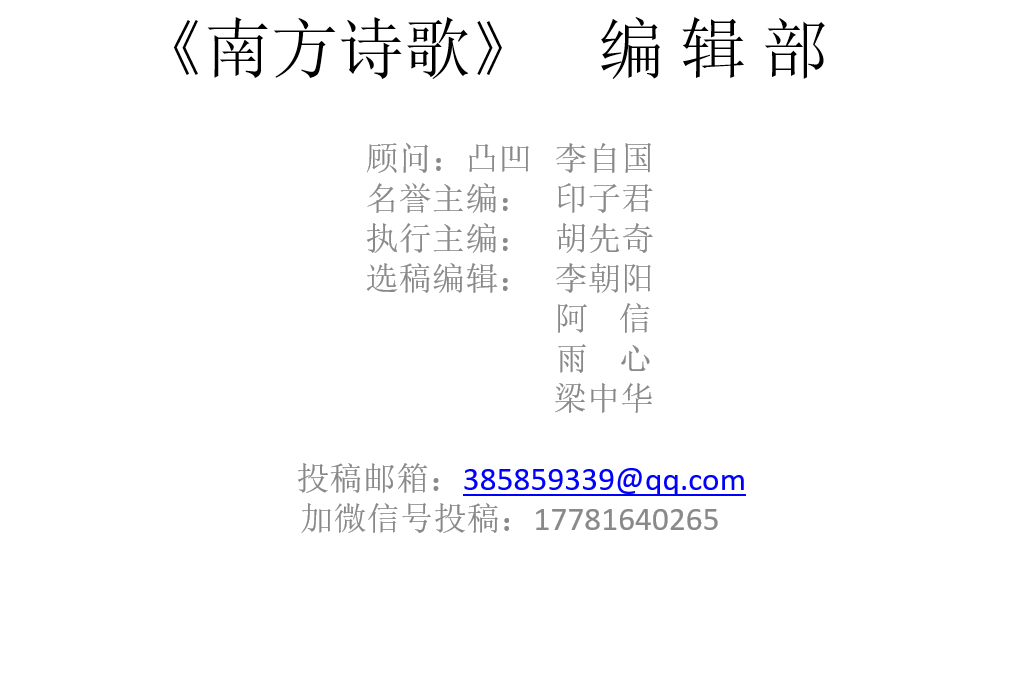
2021年《南方诗歌》总目录
2022年《南方诗歌》1月目录
“诗坛连理”:庭屹、哑石近作选
“诗坛连理”:谭毅、一行一家近作选
“张桃洲诗论”:存在的几副面孔
“张桃洲诗论”---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
”他山诗石“桑克:译诗9首
”他山诗石“:王家新最新译作选
”他山诗石“陈子弘:当代外国诗人十家
”他山诗石“汪剑钊译:俄罗斯黄金时代诗人关于冬天的诗
“他山诗石”李海鹏、石绘译:但丁《新生》诗12首
“他山诗石”高兴 译:阿吉. 米斯赫尔诗选
“珞珈诗派”黄斌:遁身于影像
”珞珈诗派“浅语纤云:液体的阳光流泻手心
“”珞珈诗派“陈O:我们生来是多么的白
“珞珈诗派”荣光启:唯有怀抱是盛装胜利的器皿
“珞珈诗派”孙雪:向星星借一双慧眼
”珞珈诗派“李金辉:在北方的大地上
“珞珈诗派”午言:边缘深陷于流动之美
“珞珈诗派”吴根友:让错过的美好如群星散落
“珞珈诗派‘夏雨:想像自己是一只狐狸
“珞珈诗派”钟立:那场错过的樱花雨
“珞珈诗派”水浅:我是你身后碎了一地的月亮
“珞珈诗派”刘焱红:大雪无声
"珞珈诗派“李浔:一只蚂蚁举着半片树叶向我走来
"珞珈诗派“上河:我们是永恒流动的肉体
”珞珈诗派“香香:面向春天 溺水或守口如瓶
“珞珈诗派”王家铭:对风景的想像
“珞珈诗派”袁明珠:追白云的人
“珞珈诗派”孟宪科:水车印象
“珞珈诗派”廖志理:秋天的边界
”珞珈诗派“袁恬:世界太小喜悦很大
霜扣儿:孤独的墓园
高鹏程:秋风赋
顔梅玖:看不见的风
张海宁:流进眼睛里的黑夜
蒲永见:永恒的雕像
龚学敏:把风箍得哭出声来
王江平:邀请一朵云来到我的屋中
高堂东溶:人性的波涛是打开一本更厚的词典
“崖丽娟诗访谈”海男:让诗的灵感从飞翔的想象力抵达现实
“90度诗点”:从历史中打开边塞--品读老房子,张媛媛
“90度诗点”--戴潍娜,张媛媛:像职业罪犯般写作
毛拾贰:那些苦难像是唇语结出的枳
李曙白:白色的沉默随波浪起伏
清平:两个人或许多人
伽蓝:与己书
徐敬亚:一粒雪就掩埋了冬天
“好诗同读”:西渡、崖丽娟评伽蓝的诗
潇潇:我的灵魂只向你弯曲
陈修元:在三亚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潘维:灵魂为什么举杯》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中国大陆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免责申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举报收藏点赞
评论
(0条)

您需要登录后才能评论,点击此处进行登录。
登录后评论
- 侨务
- 中国
- 国际
- 出国
- 财经
- 文化
④“四下基层”走访侨界困难群众|省侨联外联部赴儋州、临高、昌江走访慰问③“四下基层”走访侨界困难群众|梁谋赴东方开展专题调研中方就习近平将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答记者问|3分钟头条新闻(2025.5.4)胡允键:意大利侨二代的担当与突围——一个人、一代人与两个世界之间的连接带路东南亚|文明互鉴 粤韵生花:“粤韵杯”走进东南亚,开创华媒跨国协同传播新探索侨!我们就是这Young的青年千行百业志愿行 渝侨大爱暖人心—渝侨志愿服务队关于开展2025年“千侨助千家”活动倡议书5名中国公民在美国交通事故中遇难 | 3分钟头条新闻(2025.5.3)文博日历丨极简“宋式”穿搭 假期出游这么穿超出片
下载华人头条

关于我们
© 2022 华人头条
服务热线 : 0591-83771172
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直播备案号 闽ILS备201708250005
举报热线:0591-83771172
举报邮箱:hrtt@52hrtt.com
免责声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