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杨际岚|“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一一回望四十年前的一场论争
2022-10-02 14:24 阅读量:5.4万+
华人号:文化在线“未来的一切都
生长于它的昨天”
一一回望四十年前的一场论争
杨际岚
一
1980年2月至1981年10月,《福建文艺》展开“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
《福建文艺》编辑部于《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刋载“编者按”:
新诗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回顾新诗走过的历程和近年来的创作实践,这个问题,正在诗歌作者和读者中间引起密切的关注与深刻的思考。虽然尚未见诸于文字,实际是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的。对舒婷同志诗歌的不同看法,便反映了这种分歧。
舒婷是我省诗坛上新出现的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者,她的诗作已为读者所注目。对于她的诗的争论,涉及新诗创作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诗歌可不可以抒发个人感情;抒个人之情与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怎样扩大诗歌的题材;怎样看待诗歌的社会职能;新诗应如何吸收外来形式,这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如何;等等。我们认为:联系舒婷的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展开讨论,对于作者本人的提高,对于探讨我国诗歌的发展道路、促进诗歌的繁华发展,是会有帮助的。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积极参加讨论。
这场讨论,主要由《福建文艺》评论组出面组织,主持人是时任评论组组长魏世英先生,由蔡海滨先生具体负责。我于1978年4月从平潭调到《福建文艺》,第一站便是评论组。魏世英先生事业心和责任感很强,专业素养丰厚,十分关心爱护年轻人。他曾饱含感情回忆当年举办创作学习班和外出组稿的情景。他说:“除了参加创作学习班,我那几年有空就跑闽北建瓯、建阳、泰宁等地访问‘知青点’,体验生活,辅导创作,建瓯县的王球球发着高烧带我下乡看望知青,建瓯县的宋恒(现在笔名南强)同我畅谈生活素材和创作计划,泰宁县的陈用毅向我介绍他那个知青点的人物和故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年,我也曾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与老魏等几位编辑老师相处数日。其后,他们便出面调我上省城工作。魏先生在工作中敢于放手,让新手迅速上岗挑担子,边实践边学习边提高。我刚到《福建文艺》,便开始参与组稿,看稿,编稿。这场讨论,因而自始至终都参与了。

魏世英
正如“编者按”所说,这场讨论是由舒婷诗歌作品所引发的。魏世英先生曾于多年后回顾讨论的缘起。1979年春天,魏先生与苗风浦先生(《福建文艺》主要负责人)同去云南昆明参加一个文学会议,返程,经上海。时值思想解放运动浪涛澎湃,又逢知青回城热潮,到处热气腾腾,给了他很深的印象。那时,伤痕文学风行,在部分文学青年中还兴起诗歌创作的新潮,其中一些诗作的手抄本在民间广为流传。大约在1979年春夏之交,福州马尾区文化馆出的油印文学刋物《兰花圃》刊载了厦门青年女工舒婷的一组诗作,在文学爱好者中颇有影响。魏先生看到对于舒婷诗歌的争论很激烈,贊扬者和反对者都很起劲,便找来舒婷的诗读,开始思索这个争论的意义。他感到,舒婷的诗确实有与传统的、通行的诗歌迥然不同的新质,受到不少青年的欢迎并非偶然,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发展趋势必然要求有新的突破。因此,他两次在《福建文艺》编辑部会议上提出:厦门舒婷的诗值得注意,这些诗思想和艺术都达到较高水平,既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心声,也预示了新的诗潮在萌动,应该抓住这个典型,在刋物上开展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讨论一旦展开,必然涉及文艺理论上、文艺美学上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根本问题,可能会造成全国性影响。编辑部同仁们赞同魏先生的意见,另一方面也顾虑讨论能不能争得起来,舒婷本人愿不愿意合作,要求评论组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做好相应准备。
1979年10月初,魏世英先生和蔡海滨先生一起专程到厦门拜访舒婷。原先他们都还不认识舒婷,准备进行坦诚沟通,取得信任和支持后,再商量怎样进行这场讨论。他们由当地文友带路,到鼓浪屿舒婷的家。舒婷很爽朗,初次见面就像老朋友般谈了起来。他们在随意漫谈中把《福建文艺》要讨论她的诗这件事提出来商量。魏先生说:“讨论你的诗,不是要打棍子,目的是探讨诗歌创作问题;如果你同意,我们就一起商量着办,决不会搞突然袭击。”他还对舒婷说,你敢写与众不同的诗,敢拿出来发表,向读者交心,这里就有着不怕人们议论是非的勇气嘛。舒婷笑了。魏先生和蔡先生都表示编辑部有保护作者正当权益的责任,艺术作品的是非不允许被利用来歧视、打击作者本人。她听后又笑了:“以后出什么事了,我就去找你们保护呵,只怕到时候你们也保护不来呵。”坦诚换取了信任。舒婷终于同意讨论她的诗。我们请她先将诗作汇集寄到编辑部,以便在年内出一本油印集子,分送文学界朋友听取意见,再从中选出若干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之后在刋物上开展讨论。她爽快地答应了。没多久,舒婷如约寄来诗作,编辑部很快就印出一本《心歌集》广为分发。同时,开始为正式开展讨论筹备稿件。

舒婷
《福建文艺》1980年1月号发表舒婷的《心歌集》五首。2月号开始刋发评论舒婷诗歌的文章,自此展开历时一年八个月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编者按”由蔡海滨先生拟稿,诗歌组和评论组研究定稿。由于是“讨论”,也了解对于舒婷诗歌,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少,所以编辑部回避在按语中带倾向性,只是不带褒贬地指出,“舒婷是我省诗坛上新出现的一位青年作者”,本刊负责人苗风浦先生审稿时在“青年作者”前加上“有才华的”四个字,明确表明《福建文艺》爱护人才、扶持创作的态度。在刋物同仁们眼中,苗先生处事向来谨小慎微,不露锋芒。此次他却“一反常态”,让人颇感意外,但继而为他的热忱和坦诚所感动。讨论热烈而有序地展开,自2月号至8月号,7期刋发了17篇讨论文章。

《福建文艺》刊影
这场讨论在全国文坛引起积极反响。《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7月号以相当突出的篇幅刋载《舒婷的诗》。这一组诗作包括《福建文艺》1980年1月号所载《心歌集》,即《船》、《珠贝一一大海的眼泪》、《赠》、《寄杭城》、《秋夜送友》等5首,《诗刋》1979年7月号所载《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一一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该刋同期选载两篇讨论文章:《舒婷诗歌评赏》(作者周俊祥,原载《福建文艺》1980年2月号),《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一一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作者孙绍振,原载《福建文艺》1980年4月号,系节选)。同时,该刋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指出:“《福建文艺》1980年第2、3、4期,在《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的专题下,连续刋登文章讨论舒婷的诗作。”随后,整段引述了《福建文艺》“编者按”,从“舒婷是我省诗坛上新出现的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直到(讨论)“是会有帮助的”。本期封面提要上还以《舒婷的诗》作为要目。这样的编辑加工,显然是有意为之。以这样的位置、这样的份量推介一位年轻诗人,是极为罕见的。
鉴于《新华月报》的广泛的影响力,《福建文艺》同仁受到鼓舞与鞭策。编辑部便顺势而上,又在8月号刋出“编者的话”:
本刊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半年了。在此期间,收到全国各地的广泛来稿,得到了诗歌界、评论界许多同志的热烈支持,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这场讨论,是由于对舒婷同志的诗歌的不同看法引起的。舒婷的创作,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的现象,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评价这股新诗潮,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中争论的焦点。
深入开展这场讨论,必然地要涉及到对于我国六十年来新诗艺术传统的认识问题,也必然地要联系到在诗歌创作和评论中如何看待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抒写个人之情和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关系,抒情诗中诗人的个性和抒情主人公的典型意义,吸收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的关系等问题。在讨论中,许多文章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初步展开了。我们希望,讨论的继续深入,能够紧紧扣住上述中心问题,进一步扩展视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地进行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的探讨。
平等的、充分说理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体现。在争论中,为求得正确的认识,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反批评;同时也欢迎有创作实践的诗歌作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来参加讨论。来稿要求观点明确,论述集中,不必面面俱到,停留于泛论,文章也不宜过长。
讨论在延续。《福建文艺》前后发表“编者按”和“编者的话”,阐明了这场讨论的客观动因、基本方针和中心议题。讨论大致依照既定设想推进。为了使这场讨论更加深入,《福建文艺》与作协福建分会于10月15日至25日在福州联合召开新诗创作讨论会。本省38位诗歌、评论作者和编辑与会,同时,还邀请了《诗刋》杨金亭、社科院文学所楼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宫玺、姜金城、《文汇增刋》罗达成、湖南《湘江文艺》李元洛等出席。魏世英先生后来撰文称:“这次盛会立足本省,面向全国,采取刋物讨论与会议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诗人、评论家与编辑面对面交流探讨,本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各抒己见,自由争鸣,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扩大了这场讨论的影响,也使《福建文艺》在全国文学期刋中有了知名度。”

《福建文艺》1973年试刊号
曾任《厦门文学》副主编的谢春池,在《我是〈福建文学〉同龄人》一文,从会议合影,这“此生拍的第一张彩照”,回忆到会代表,除省外几位外,有《福建文学》的苗风浦、郭风、何为、魏世英、陈钊淦、蔡海滨、朱谷忠、杨际岚,本省的孙绍振、刘登翰、周美文、陈中、练文修、张元锦、范方、俞兆平、王者诚、孙新凯、陈瑞统、陈志泽、黄文忠、夏雄、王性初、薛宗碧、周俊祥、蔡荣电、陈仲义、林祁、翁友本、崔晟、施敏华,部队的邢书弟等,以及舒婷本人。尚有因故未参加合影的蒋夷牧、陈志铭、王光明。该文说,“此次会议空前活跃,也十分自由,双方舌枪唇战,前所未有的激烈……”在他笔下,一位诗人“慷慨激昂地站起来,手拿数页讲稿,一口气质问了几十个为什么,后被称为‘高炮诗人’。”他说,记得孙绍振说了一句很抒情很优美的话:一条手帕从阳台上飘落也有它的美学价值,此话那一刻拨动了他的心弦……他的一段描述可谓这场自由论争的生动写照:“与会者会上是敌手,也难免把各自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带到会外。那时的男人大都还穿中山装的,也有穿上海装的,极少穿西装的,这次会议,似乎只有我一人穿西装。记得某天上午会后,孙教授尖刻地嘲讽我:谢春池,你穿得这么现代,却那么传统?我即刻反击道:老孙啊,你那么现代,却穿得这样传统!一时驳得他哑口无言,朱谷忠在一旁嘿嘿笑了起来,我们的教授中山装一式的衣领正扣得紧紧的。不过,会外我们相处得很好,都是朋友,有许多的交流。”
这场讨论引起诗歌界、评论界的关注,省内外不少知名学者、评论家纷纷撰文参与。如范方《感情真挚的歌声》,蒋夷收《用自己的的声音歌唱》,孙绍振《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朱谷忠《关于舒婷的诗及其他》,黄勇刹《发现和创造》,方顺景、何镇邦《欢欣与期望》,雁翼《抒情诗中的诗人个性》,杨匡汉《愿新人们走向成熟》,刘登翰《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俞兆平《诗,向着人的内心世界挺进》,徐敬亚《新诗一一行进在探索之路》,钟文《让诗回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吴思敬《新诗讨论与诗歌的批评标准》,费振刚、方克强《时代精神与表现自我》,等等。同时,也有普通读者读了刋物上发表的批评舒婷的某些意见,提出商榷,踊跃参加讨论。比如,有的文章说,“她(指舒婷)诗歌中的感情,有的纯粹是她自己的,有的是一部分青年人的,但绝不是一代青年,一代人的感情”。“署名“林云”的读者则回应,“‘她’自然代表不了全体人民,但‘她’却是全体人民中的一员,‘她’唱出的是自己的‘心歌’,这种‘心歌’不是恒定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们理解并尊重读者的“一得之见”,同样适时在刋物上发表。正如“编者按”和“编者的话”所说,“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积极参加讨论”,“平等的、充分说理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体现。”
不少文章,联系舒婷的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地进行有系统、有深度的探讨。假如借用上述几篇文章的篇名,概括起来,这些意见,本人认为,确实值得重视:(舒婷等勇于探索的青年诗人)“用自已的声音歌唱”,(这是)“感情真挚的歌声”;(这些作品)““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对于他们,滿怀)“欢欣与期望”,“愿新人们走向成熟”。
二
有学者认为,1980年是新诗发展的关键转折期。这年4月召开的南宁诗会是建国后首次专门针对新诗举行的全囯性大型学术讨论会,“南宁诗会上对朦胧诗不同的认识与评价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争论促进了朦胧诗的全面崛起。”杨匡汉先生近期于《又向长亭寻断魂》一文对诗会上的争论作了形象的描述。“在大会发言时,谢冕把春天的鲜花送给了舒婷、北岛、江河、顾城等当时诗坛来不及认识又遭到非议的年轻人:‘热情地扶植他们、指导他们吧,给他们以发表有异于众的、初看不免有些古怪的作品的权利吧!……对待青年人,要严格,不要歧视。但目前更需要的是宽容和慈爱。”谢冕先生事后应约撰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并在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文艺版头条发表。邵燕祥笑称,此乃谢冕的“五七指示”。杨匡汉先生又写道,“南宁诗会的另一位‘明星’是孙绍振。机敏的辩才孙绍振,自称他的强项是‘吹牛’和‘放炮’。这次南宁诗会安持他大会发言,竞滔滔不绝地从新诗发展史讲起,一一评说众多诗人的成败得失和不同主张的各自局限”,说着说着,台下的诗人黄勇刹坐不住了,“边唱山歌边走向讲台,打断孙绍振乱放炮,说‘你一派胡言,使我想起了饥饿年代骗人的小球藻。你完全是小球藻理论家!’接着,以民歌的优势和孙绍振理论了一番。争鸣的气氛热烈起来,孙也绅士地给黄鼓了掌。”黄勇刹,时任《广西文艺》编辑部诗歌戏剧组组长、中国民文协广西分会理论组长,擅长诗歌创作和民歌研究,彩调剧剧本《刘三姐》作者之一。他也参与了《福建文艺》的这场讨论。他的《发现和创造》刋载于1980年6月号。此文表示,读了舒婷的《心歌集》,“我的心情是非常振奋的,”“我感到作者的发现能力是有点非同凡响的,”“舒婷同志的歌声是真切动人的,基调是健康向上的,朴实而且明朗的”。黄勇刹文章又说:“另一方面在这丰硕的成果里,也还存在不少美中不足之处。比如说,在肯定作者的诗的基调是明朗、向上的同时,我仍感到它有些迷惘,有些低沉。在思想情调上,甚至在艺术技巧上,有洋多土少、土洋结合得不够理想的毛病。”他的意见,在一些论者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文文末署上写作时间:1980年4月6日南宁。此后南宁会议上,他的意见相较显得较为激烈。但是,总体而言,各方论争,大多限定于艺术范畴,体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年底,由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丨诗探索》创刋。闽籍评论家发挥了突出作用。那时,张炯系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谢冕系《诗探索》主编之一,孙绍振担任编委,刘登翰也积极参与。改革开放以来,谢冕、孙绍振、刘登翰等在诗歌评论界具有广泛影响。他们的理论主张深刻影响了福建诗坛。

谢冕
《福建文艺》(《福建文学》)讨论中,编辑与诗人、评论家展开良性互动。魏世英先生后来回顾时说:“在这场讨论中,我与舒婷友好合作,很愉快也很有成效。许多读者写信给舒婷经由〈福建文艺〉编辑部收转,舒婷委托我先拆看,供讨论时参考,然后再寄给她。许多未曾谋面的青年读者热情洋溢地给舒婷写信,敞开心灵倾诉人生的遭遇和郁积的情愫,我有幸先睹为快,从中了解社会、咀嚼历史、体味人生,获得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他认为,“新诗潮的兴起并非偶然,其中蕴含着的悲哀和愤怒、觉醒和思考,反映了一场浩劫之后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愿望,用所谓'朦胧诗派’来统称新诗潮我以为并不确切,既没有肯定其历史价值,也不能说明它表现时代生活的特质。”他后来从舒婷那里借了更多读者的信来阅读,打算利用这些资料,研究“舒婷和她的读者”。魏先生感慨地说:“这个题目是‘诗与人民’的特殊视角,可以做出很生动很深入很丰富的文章。可惜又是时过境迁,无暇顾及,把它放弃了。”
舒婷出于对编辑部的信任,帮助约到青年诗友写的十则《青春诗论》,发表于《福建文学》1981年1月号(从这一期起,《福建文艺》改刋名为《福建文学》,魏世英先生转任该刋副主编)。编辑部在“编者按”中说:“本刋开展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将近一年了。今年,我们打算将这场讨论持续下去。这一期,集中发表一组青年诗人论诗的文章。诗坛上新人辈出,不但以各呈异彩的诗作引人注目,而且有关于诗的新鲜的、精彩的见解值得重视。当然,有些意见还可以讨论。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这就能够使我们的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十则《青春诗论》是:杨炼,《我的宣言》;徐敬亚,《生活.诗.政治抒情诗》;顾城,《学诗笔记》;高伐林,《探索之余谈探索》;李发模,《学诗断想》;张学梦,《关于诗》;骆耕野,《诗和诗人》;梁小斌,《我的看法》;陈仲义,《颤音》;王小妮,《我要说的话》。

孙绍振
此后不久,《诗刋》连续载文批评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福建文学》(及其前身《福建文艺》)开展的讨论,议题相近,是否会波及?难免引起担忧。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5月12日至18日,作协福建分会、《福建文学》编辑部在福州联合召开了青年文学作者座谈会。我受托写了综合报道,刋载于《福建文学》1981年7月号。因而,当年场景得以还原。座谈会上,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项南同志作了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讲话。根据那时所写的报道稿,讲话要点如下:
项南同志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形势是好的,创作了一批很好的作品。可以说,思想刚刚解放,文艺园地刚刚萌芽,大地刚刚苏醒。我们写作品,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自己,人民需要精神食粮,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应该起到鼓舞、引导群众的作用,不应给人消沉、沒有出路的感觉。有少数作品沒有很好地起到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极个别作品有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即使是出现这两种情况,我们对作者,还是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处理文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积极引导、疏导的办法,采取和风细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要简单粗暴,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人是可以批评的,问题是怎样批评。要么不能批评,要么一批评就“批倒、批臭”,这是极不正常的风气。他还指出,福建在历史上、在现代都涌现了不少科技、文艺等方面的优秀人物,希望在文学艺木方面能出人才,放异彩。中央允许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这方面,文艺应当吹起号角,起到鼓舞建设者的作用。他勉励代表们为社会主义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繁荣福建省的文艺事业。
聆听项南同志一席话,如沐春风。
综合各方面情况,魏世英先生邀集评论组同仁,商议结果是讨论继续,不表态。之后,每期发一两篇文章,持续到10月号,随后就悄悄结束了。魏先生说:“我们沒有给‘讨论’做总结,我考虑总结并不好做,还是留给历史去做为好。”同年11月号,载文《浸透爱国深情的含泪歌声一一谈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作者林锡潜),以推介舒婷优秀诗作的方式,充分肯定年轻诗人的探索精神。
三
当下百度百科上,关于孙绍振先生的条目这样写道:“……日后的实践证明:孙氏的这一论文(注: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已成为当代新诗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到九十年代中期,已经为一系列当代文学史所肯定,其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这里说的“当代文学史”,如《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书中写道:“‘朦胧诗’并不是突然崛起的,它有着长期酝酿、积淀的过程。”“最初,围绕着‘朦胧诗’进行过一些论争。许多报刋都开辟了论争专栏,如《福建文学》对舒婷作品的讨论,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有评论家更是直言不讳:‘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注:指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在当时,能从美学嬗变的角度来看待与阐释‘朦胧诗’,无疑是具有长远历史眼光的。”又如作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中华文学通史》,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书第八卷更为具体地描述了关于“朦胧诗”的三次理论上的大争论。关于第一次争论,该书写道:“争论最早在‘朦胧诗’派重要诗人之一的舒婷的故乡展开。一九七九年,福州市马尾区的刋物集中发表了舒婷〈珠贝一一大海的眼泪〉等五首诗。〈福建文学〉随即围绕舒婷的创作,开展了‘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后来结集为《新诗创作问题讨论集》一一附:舒婷《心歌集》。”“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将舒婷作为‘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来评价,并提倡对这股诗潮进行分析。在为期一年多的讨论中,《福建文学》共发表了三十多位诗评家的文章,引起诗坛的关注。”书中继而介绍了1980年4月南宁诗会的第二次论争,1980年9月《诗刋》举办“诗歌理论座谈会”的第三次论争。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
诗坛许多知名学者对这场讨论给予充分肯定。诗评家刘登翰先生于近期回顾论争时说,“我在1980年第12期的《福建文学》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一股不可遏制的新诗潮一一从舒婷的创作和争论谈起》,这是我有关朦胧诗论争五、六篇文章中比较重要的一篇,201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历史档案》一书,曾收入该文”。诗评家杨匡汉先生日前告诉笔者,他在讨论中发表的《愿新人们走向成熟》,陈敬容(著名九叶派诗人)曾致信对此表示贊许。诗评家古远清先生则直言:“此讨论率先提出‘新诗潮’概念,影响深远。”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也不断与时俱进。作家谢春池坦言,当年在关于舒婷诗作的论争中,基本上属于否定者阵营,这么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我的谬误,我也对从前的谬误进行了改正。”

刘登翰
《福建文学》的各位编辑同仁,都分外珍惜在新时期文学大潮中搏击的难忘历程。时任副主编季仲(后任主编,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曾在追忆魏世英先生编辑生涯时,深情回顾了这段经历:为了广开言路,深入探讨,老魏与本刊编辑一般都不泄露自己的倾向性,保持着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态度。直至讨论进行将近一年,老魏见到反方有些看法过于陈腐、偏执而且上纲上线,这才以“边古”为笔名写了《从舒婷抒什么情说到“善”》一文刊于当年第11期《福建文学》。令人诧异并深怀敬意的,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之初,作为一位探索者的“魏拔”(笔者注:系魏世英笔名),已经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来阐释舒婷诗歌的“善”,又用马克思主义“异化”学说来分析舒婷的《流水线》。于此两年七个月之后,周扬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以长篇宏论阐释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这才引起一些权威人士的大惊小怪。可见这位外表沉静安分的谦谦君子的思想是相当敏锐而前卫的。季仲先生又写道:“在这里我还要透露一个秘密:在那场大辩论中,老魏与舒婷书信来往频繁,此后同在文联工作也不乏见面机会,但老魏从未在舒婷面前提及曾用笔名‘边古’发表为她辩护的文章。他的兴趣惟在探索,惟在办刊,至于当代伯乐或护花使者之类虚名,则从来未敢掠美。惟我作为老魏的同事,遥想往事,当诗坛一颗新星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如果视而不见漠然置之,《福建文学》将会因此蒙羞并深感遗憾。”读到此处,不能不令人动容!蔡海滨先生当时具体负责讨论工作,后曾任《福建文学》主编。他在讨论开展10年后的《福建文学》1991年5月号,撰文道:“福建也曾被称之为‘朦胧诗的策源地’,还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闽籍评论队伍和香港作家群。由《福建文学》发起组织的新诗创作问题讨论,历时两年,波及全国,是新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诗歌讨论。它促进一代诗人的成长,为新诗创作拓宽了领域,也把诗歌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孙绍振先生在《福建文艺》讨论中撰写的万余字论文《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有三节,即“第一,关于情调的低沉和高昂的问题”,“第二,关于新诗中的自我形象的传统问题”,“第三,关于外国诗歌影响和民族风格问题”。此文刋载于本刊1980年4月号,随后为《新华月报》(文摘版)转载,选用其中第一、第二节。基本理念与其后撰写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脉相承。如今重温,或许仍不无启迪之处——“舒婷所塑造的自我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她揭示了一代青年从沉迷到觉醒的艰难和曲折。当然她所表现的并不那么完整和明确,但是她还是在我们新诗画廊中增添了一个新角色,一个非英雄的平凡的角色,但又往往以英雄主义勉励自己的以陌生而特异的丰彩而引起了注意的角色。”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批一反这些积弊的新人。”“舒婷应该说是这类作者中的优秀的代表。她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但是她的风格却来自我们的过去。”“……(她)从具体的有个性的人出发,从溶解在真实心灵中的真实生活出发。她虽然力图更深地反映生活的内在本质,但是她更注意那特殊的自我形象的心灵的活动,着意表现其敏感和智慧。”
“舒婷继承的正是这种把展现人的独特的心灵的真实放在第一位的艺术传统。”“……为了解放诗人的个性,钻研一下舒婷代表着的新人的作品,温习一下新诗这一优良的艺术传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新诗的艺木传统不限于此,但这点无疑是最重要的。”
同期《新华月报》转载的,尚有舒婷的诗作《这也是一切一一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这里引述于文末,也许有助于人们回望过往,继续前行: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夜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沒有回响;
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
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的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1977年7月25日
(2021年5月)
❖
作者简介:杨际岚,平潭人,中国作协会员,编审(二级专技),1978年4月至《福建文艺》(《福建文学》)工作,1984年6月参与创办《台港文学选刊》,历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台港文学选刊》主编、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等,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两岸视点》编辑总监、《海峽乡村》编辑顾问。散文随笔、杂文、纪实文学、文艺评论等时见报章、杂志,并著编出版作品集多种。长期致力于促进海峽两岸和海内外文化交流。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杨际岚|“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一一回望四十年前的一场论争》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希腊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文化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免责申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举报收藏点赞
评论
(0条)

您需要登录后才能评论,点击此处进行登录。
登录后评论
最新资讯
热门排行
下载华人头条

关于我们
© 2022 华人头条
服务热线 : 0591-83771172
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直播备案号 闽ILS备201708250005
举报热线:0591-83771172
举报邮箱:hrtt@52hrtt.com
免责声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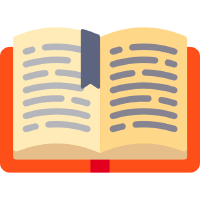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