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好诗同读”:西渡、崖丽娟评伽蓝的诗
2022-01-24 00:00 阅读量:7k+
华人号:南方诗歌
“荆棘林立着勃勃生机……”
——伽蓝略论
西渡
伽蓝的诗让我吃了一惊。在这本诗集之前,我没有读过他的诗。刚开始,我多少带着一点挑剔甚至轻慢的态度。当我在第一辑里读到《刷漆工的坚韧》《加冕礼》《人民》《每天早晨都找到一个莎士比亚》《经验》《遗言》《现在,他感觉》《树枝摇曳》《林中水滴》《七日书》《为何要写作》《下山》《两个孩子》《汉语之光》等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诗人。等我读到《暮色》《初冬,我从它们中间走过》《日课》《乡巴佬》《一头骡子》《个人美学》《春风不度》《早晨》《对所爱又能说什么》《每一秒都很珍贵》《星空盖顶》《马之诗篇》等一系列诗作,我已经被这个诗人征服了。这些诗有的是非常出色的自然诗,有的有力地表现了独特的生存经验,还有的可以列入这个时代最好、最深情的情诗。伽蓝的诗形式凝练、手艺老道,内容结实,是艾略特所说的那种既有话要说,又发明了自己的说话方式的诗人。这样的造诣在很多名诗人也未必达到。读伽蓝的诗是我近几年最愉快的阅读经历之一,时时有发现的惊喜。
伽蓝生于1976年,迄今还是一个无名的诗人。他很少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之前虽然出版过诗集,也几乎没有引起注意。而和伽蓝同龄的很多诗人早已名声在外,在公众中树立了自己的诗人形象。比他年轻的一众80后诗人、90后诗人也早已在各种媒体频频亮相。已过不惑的他还在寂寞中写作。然而,他却是一个老资格的诗人。从2004年开始写诗,伽蓝一直是一个高产的诗人。据他自己统计,2004年写诗10万字,2005年8万字,2006年10万字。之后,产量有所下降,但也一直笔耕不辍。2016年以后,伽蓝的诗歌创造力再一次爆发,仅2018年就写了1万多行。我们的诗坛对这样一个诗人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个事实一方面令人高兴,因为它说明当代诗坛充满生机,藏龙卧虎;另一方面它也令人羞愧,因为它说明诗坛依然是势利的。下面我就试着总结一下我对伽蓝诗的阅读印象。
“所有的根,都攥紧血块般的泥土……”
瑞典诗歌评论家扬·乌拉夫·于连在评论女诗人安娜·吕德斯泰德的时候,揭示了女诗人身上存在一种植物性的“卑贱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一种“单纯的美和丰富性”,体现了“坚忍不拔的生命的非凡奇迹”。[1]我们可以据此区分两类诗人,一类是热衷于漫游的、动物习性的诗人,他们的生活空间不断变化,写作的题材、风格、主题变动不居;还有一类是倾向于定居的、植物习性的诗人,他们一生很少离开一个地方,写作的题材、风格、主题也相对稳定。惠特曼可以作为前一类诗人的代表,狄金森可为后一类诗人的代表。[2]从生活阅历和收入这本诗集的作品来看,伽蓝大概属于那类植物性的诗人。伽蓝是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人,在门头沟山里长大,15岁到18岁到门头沟龙泉镇求学,之后又回到山里从事小学教育,直到2013年调到龙泉小学,伽蓝在门头沟山里整整生活了34年。他的诗就是在这样一个山里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和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北方大山里的人们为了朴素的生存所进行的劳作、挣扎,他们的希望和爱恋,他们的思虑和忧心,便成为他的主题。当然,这些人们中就包括了诗人自己。也正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能把这个世界的经验表达得如此真切生动。在我看来,无论从表达的精湛还是表现的深度来讲,伽蓝的这个诗歌世界都是当代诗歌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存在。
北方的山,和南方山水映带、秀媚迷人的山大为不同,往往到5月还一片枯索,10月过后就木叶飘零,一片荒寒了。门头沟的山又多是光秃、峭拔的石山,一年到头难见绿意。对于这种荒芜的情状,伽蓝有最好的表达:“三五百里石头/垒着走不尽的荒凉”(《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这种荒凉足以让“少年在民间白头”(同上)我因为妻家曾在门头沟居住,去门头沟山里的次数不少。面对那些巍峨却了无生机的大山,我大抵完全失语。对伽蓝,这些荒凉的大山一开始也并非什么诗意的存在。他自己交代,“到过门头沟区的人都被门头沟连绵不断的群山所震撼。但是,这些山对我造成的压抑感是无以复加的。尤其到了冬天,万木萧瑟,荒凉感袭来,全是穷山恶水。”但是有一天,他“从山外听课归来,望着陡峭的山影,竟然恍惚起来”,“荒凉的山影成了宋代的笔墨,枯涩的荆棘林立着勃勃生机”。[3]从原本巨大的荒凉中看出“勃勃生机”,这是伽蓝感受力的一次蜕变,也是其看待事物方式的巨变,更是精神上的蜕变。从这一天开始,伽蓝才真正拥有了这个大山的世界,这些大山也从压抑、负担变成了财富。这个大山的世界和伽蓝开始彼此拥有,他的诗从此有了自己的根系。这个根系深扎于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从中汲取珍贵的养分,长出了一片结实遒劲的林木。这是属于北方的林木。用伽蓝自己的诗句说:“所有的根,都攥紧血块般的泥土”(《乌有乡》)。而在这根系的上方,是予贫苦的人们以安慰的“渴慕无限绵展/所有手臂都向上”的北方的土地和天空。伽蓝解释“本”的意义,“是草木的根部,用灵魂吸取土地中的黑夜并酿造某种风景”(《在纸上》)。这话说出了伽蓝诗世界最大的真实,它有本、有根,酝酿于黑暗的土地,而贡献给我们某种灵魂的风景。
这个集子中收入不少伽蓝写山的诗篇,无不透出北方山水那种从荒凉中涌现的勃勃生机:
树枝摇曳,毛茸茸的鸟声
点缀清澈见底的绿意
涧底的琴声无人弹拨自己鸣响
终日不绝。山风徐徐吹过
而鸡犬并不相闻。
掐灭了烟头,忽然有
躺在树尖上随风摇曳的冲动
在山腰望一望,脚下的初夏
涌动,层层波浪此起彼伏
——《树枝摇曳》
它看见,岩石上的树影
与落叶上的树影
都穿着一件光的礼服
质地,经验与性情不同
显示不同效果。尤其山风
吹来的片刻
岩石上的树影默默颤抖
落叶上的树影,在弹唱野歌
——《林中水滴》
《树枝摇曳》写北方初夏的山,“毛绒绒的鸟声”“涧底的琴声无人弹拨自己鸣响”“在山腰望一望,脚下的初夏/涌动,层层波浪起伏”,这些描写都紧扣了北方初夏之山的特征,既不能移之于南方的山,也不能移之于其他季节。这是感觉的精准呈现,有某种变形,然而分寸拿捏得当。《林中水滴》写秋山,而出之于林中水滴之眼,构思精巧,描写精确。“岩石上的树影/与落叶上树影/都穿着一件光的礼服”,若不从水滴之眼看,描写便浮泛,而出于水滴的视角,就是精确。《听泉》写北方山中冬天被冻住的泉水,“白色泉水是倒挂下来的爆炸”,也非常传神。另一首《下山》写登高者下山的心理状态,语调、节奏和心理感受配合精妙,心理上的秘密活动被呈现为声音上具体、精细的感觉:
下山比上山更快
一个人没有了秘密和欲望
身体就会变轻
为一座山写了一首诗
就会更轻一些
现在,健步向下
像跳跃的山羊
谈到伽蓝写山的诗,当然不能略过那首这本诗集标题所自来的《加冕礼》:
“死者会被加冕。”之前他摸黑
走过最后的路。直至戴上野花的王冠
鸦雀无声的时刻,真正的平等在闪耀
日月以沉甸甸的钢印压迫树林的法庭
山谷中的所有野花,献出自己的火焰
与金属。怀着惊惧,提取雨滴里高贵的语言
这是第一仪式,直到那天。祂,为我加冕
这首诗在收入诗集之际,诗人作了最后的加工,把原来的十四行改成了七行。为了便于对照,我把上一稿附在下面:
“死者会被加冕。”之前
他摸黑走过最后的路
直到戴上野花的王冠
鸦雀无声的时刻
真正的平等在闪耀
日月以沉甸甸的钢印
压迫树林的法庭
此时,山谷所有野花
都献出自己的火焰与金属
怀着惊惧,提取
雨滴里高贵的语言
这只是第一道工序
……直到那天,它们
准备为我加冕
改后诗行加长了,差不多等于把原来的两行合成一行,两行之间加了空行。诗行的合并让每一行的意思变得更为完整,空行又使空间疏朗,让形象和意义都得到强调。字句上也有一些改动,原来较为抽象而力量稍弱的一行“这只是第一道工序”改成了“这是第一仪式”。“第一仪式”比“第一道工序”更为庄严,而且“第一仪式”有“最重要”“无与伦比”的意思,是“第一道工序”无法体现的。“这只是”意味着第一道工序之外,还有第二道工序、第三道工序,分量就轻了,改为“这是”,表达更准确——实际上,是意义本身得到了澄清。“这是”也比“这只是”更简劲有力。“它们/准备为我加冕”改成了“祂,为我加冕”。原句的“它们”指代稍微模糊,根据上下文,可以指野花,也可以指语言。如果是前者,为“我”加冕的是自然;如果是后者,为“我”加冕的则是语言。改后,为“我”加冕的则是神圣的“神”。这个“神”,在伽蓝的诗里,是自然和语言的进化,也是对第一行所说的“死者会被加冕”的呼应。“死者会被加冕”可以理解为死亡为死者加冕,然而,诗人最后告诉我们,为死者加冕的是“神”。由于最后的这一转,全诗风格更为庄重和严肃了。这首诗原来已非常好,修改之后,就更好了。这个修改也见出诗人在技艺上的锤炼功夫和自我要求之严厉。实际上,这本集子里最好的那部分作品大多经得住技艺上的严格挑剔。也许我该提醒读者,这种技艺上的品质绝不仅仅是技艺的,而是诗人的精神品质的显现。一个技艺上粗糙,满足于差不多的诗人,其精神品质也是靠不住的。
这首诗可以看作诗人的人世道路的一个象征。在伽蓝看来,诗人在人间的天命就是摸黑走路,而且这种状态是不会改变的,直到诗人的肉身陨灭,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只有到那时,诗人才会迎来一生的荣耀时刻:“真正的平等在闪耀”,“山谷中的所有野花,献出自己的火焰/与金属。”而在此之前,诗人的命运就是:“怀着惊惧,提取雨滴里高贵的语言”。这一工作的奖赏就是在肉体死亡的那天,“祂,为我加冕”。伽蓝非常自觉地择定了这样的命运。他说,“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被诗歌选中的人”。[4]这不是自封天才的狂妄,而是一种义勇:在众人逃避的时刻,作为侍奉者,承担起诗人时时惊惧的命运。对于真正的诗人,才能不是自傲傲人的资本,而是献身的召唤。这就是臧棣所谓天赋之债的意义。伽蓝的自然诗中,特别值得提出表扬的还有那首无与伦比的《星空盖顶》:
发光的院子熄灭以后
你仍然不能看见
仿佛天空并不存在
只剩下黑暗
铐住深不可测的时间
必须容忍自己
也变得漆黑
让呼吸进入黑暗内部
承载消失的身体
天地这样辽阔
从来都是一人来到
现场的黑暗发掘
然后,繁星
闪烁,一条大河翻卷
亿万颗孤独的星体
你感觉自己又矮了
三分之一,而所有一切
将在这一刻填补你
失去的部分
当代诗中写星空名气最高的要数西川那首《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写于1985年),这首诗入选各种选集之多,甚至引起了作者的抗议。青藏高原上,“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上空的星空,让诗人变成了“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这是一个自然的、远方的、绝对的星空,以其神秘和永恒征服了诗人,也征服了读者。伽蓝笔下的星空全然不同。它不是一个超越的、普遍的星空,而是一个具体的、经验的星空。这个具体体现在空间上。它是作者所居住的院子上方的星空,是一个被灯光、雾霾所埋葬的星空。在院子里的灯光熄灭之后,你依然看不到它。这样一个星空,必须依赖人的发掘能力,而其前提是“必须容忍自己/也变得漆黑/让呼吸进入黑暗内部”,直到让自己的身体消失。只有当人完全消失于黑暗中,星空才会显现:“繁星闪烁,一条大河翻卷”。这个具体也体现在时间上。什么时间?一个中年的时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人生到了中途,前前后后都是一样茫茫”,需要人“用一半儿的命在活,用另一半儿的命去死”的时间。[5]在这个时间里所看到的星空,当然不同于西川在二十郎当岁所看到的那个绝对的星空。这个时间是从死中去发现活,从无中去发现有,从黑暗中去发现光的时间。伽蓝的“星空盖顶”就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向人显现的。它当然是空间的,但这个空间容纳了心理和经验,容纳了雾霾,容纳了人世各种各样的脏。这个经验的星空不会把人变成领取圣餐的孩子,而是让你“感觉自己又矮了三分之一”,并且“填补你失去的部分”。那个领取圣餐的孩子不曾失去过什么,也没有多少可以失去,而这个在自家院子里眺望星空的人却饱尝失去的滋味,而且随时面临失去。因此,星空对他呈现了更为神圣的价值,是把他从黑暗中挖掘出来的命运所系的事物。两相比较,西川的诗分量就显得轻了。我们要感谢伽蓝,在三十多年之后,终于可以使我们忘掉西川那首著名的诗了。
从视觉神经生理学来看,黑暗不是一个否定性的观念,而是视网膜“制性细胞”(有人译为“停止神经元”)活动的结果,是视网膜的产物。阿甘本因此认为,“感知黑暗并不是一种惰性或消极性,而是意味着一种行动和一种独特能力。对我们而言,这种能力意味着中和时代之光,以便发现它的黯淡、它那特殊的黑暗,这些与那些光是密不可分的。”[6]就伽蓝这首诗而言,其突出和令读者感到惊心之处正体现在它对黑暗的深入骨髓的感知。正如从北方大山的荒凉感知其勃勃生机意味着诗人感知力的解放和提升,这种感知黑暗能力的获得意味着诗人灵性上的一次翻越,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和世界签订了一份新的合约,一种全新的权利和义务将依据这一合约而展开。
“它们驰行于苦役中……”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拥有感知黑暗的能力意味着诗人的存在状态从天真进入到经验,从诗学的角度,则意味着诗艺上从单一、单纯到综合的转向。这种综合的一个含义是,词语、经验、想象都依据某种设计比例(此一比例当然要视主题、题材、情绪而变化)在诗中得到合理的配合。在这一“综合”的诗人之眼中,万物也拥有了其复杂的性质。按照前引阿甘本的看法,这种复杂性并非事物本身所有,而是诗人独有的内在神经元感知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诗人依据创造的原则(以想象为中介),把自身经验、情绪、感觉的复杂性——一言以蔽之,心智的复杂性——赋予万物的结果。在某个时期,伽蓝大量写到各种动物,他写骡子,写马,写牛,写蚂蚱,写金鱼,写麋。很明显,这些动物都和人/诗人的世界保持了密切的、经验的联系。在伽蓝笔下,这些动物全都成为了人的经验的承担者,人的劳动、苦难、美和罪恶的承担者。在它们的形象中,人的生命和存在的各种状态以变形然而高度真实的形态呈现出来,而得以成为我们反复凝视的对象。
伽蓝的《一头骡子》写年老的骡子即将面临被杀的下场。诗人对这命运没有加以渲染,仅略加暗示,一次在开头,“驾驭它的人/也是杀它的人”,一次在中间,“杀它的人躲在远处的屋檐下”,然后诗人仿佛忘记了这件事似的,径自写起“杀它的人”热热闹闹地在“吃一碗热汤面”,与此同时,雨中的玉米地喝水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而“对面山梁上的松树林/氤氲着一团/化不开的阴云”。生的热闹与死的荒凉、绝望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存在的荒谬与残酷就在对照中得以揭示。
《马之诗篇》是一个包括七首短诗的组诗,写尽了马的生与死,而其中四首出以马的叙述,与前人、今人的马诗都不一样。《小时候》写小马对于“成人”生活的猜测:“会长出翅膀飞越树林/在月下饮着冰水/有着吃不完的鲜草/每种草都有不同的香气//值得一生回味。”然而,有时它也被瞌睡“那穿透一切的引力”所困,感觉到道路漫长:“每一条路都是一生的长途/山岗,一个单调的存在”。它最大的安慰是,“好在背上没有鞍鞯/颈上没有绳索,在最初的时候”。这首诗把小马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其动机是一种深沉的同情——事实上,真正的诗都根源于这种同情——诗人借此得以真正进入小马的生命状态。《同谋》写马、道路和人的纠葛,“道与人也构成同谋/当马队低着头,一次次/走过自己的愁肠/怀着消磨殆尽的敌意”。道和马的愁肠互喻,传达出丰富的意涵。“它们驰行于苦役中,创造/无人知道的故事”,在这样的苦役中,“活下来,融入风景”就成了一种庄重的承诺和信念。在存在的意义上,马和马背上的人也是一种互喻。《中午时光》写马的瞌睡,这瞌睡是艰难行旅中的短暂休息,然而也是人间苦难的象征:“连蹄子也沉入瞌睡/在路边,臣服于一根缰绳/几只苍蝇//眼皮是最重的现实/一重山到另一重山的长度”。然后,被惊醒了,“转身,铃铛在老路上响/……/背上的人/在笑,而我只是走在厄运里”。连马的阴影也无法摆脱这厄运,“骑士的影子也骑着它/掠过一切,始终无法摆脱/始终,一个谜,一个刺”(《阴影》)。于是,马/诗人一同感叹:“许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文字,否则大地将写满/碎玻璃般的叹词。”(《大沙耶子》)与上述诗篇着意表现“马路”艰难不同,《雨天》写出了行旅中那些短暂的幸福时刻。在这首诗中,生活中片刻的闪光被雨水召唤出来:
树林安静。我弹奏全世界的露水
沙棘的刺是一个泛音
野罂粟,柔板。蓟草上升起了华彩
每一步都溅起叹词
在下山之前,桦树的叶子
闪着光。野草举起火焰般的喊叫
苔藓装饰低音
美,到达了缓缓运动的骨骼
这个高峰时刻催生出一种伟大的意识:“生命真实,万物共用一个身体/夏天在眼睑上/秋天拱起明亮的门廊”。这是“马生”的高光时刻,在这一刻,苦难被征服了,世界显出最为迷人的一面,马/人/世界达成和解而彼此注入。
在这样的诗篇中,伽蓝一方面通过山水、植物、动物表现人的存在,而诗人/人也经由山水、植物、动物而丰富了自己,扩大了自身存在的界域。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因这种融合而一起上升到一个新的领地——就像大地上的熊进入星空变成大熊星座,猎人化为猎户星座一样,嫦娥奔上了月亮。这中间存在维度的差别。而多数的诗人并无这样的力量,在他们笔下,熊还是熊,猎人还是猎人,嫦娥还是一副沉重的人间之身。这是诗人才能的标志,也是诗和散文的分界。
伽蓝也有很多诗直接表现人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属于底层的,却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普遍的,其唯一的条件是读者的同情心。在《人民》中,伽蓝写道:
被连续锤打的钉子
直立着楔入
木头的沉默
一个陌生的位置
箍紧的黑暗
像冷酷的资本家压迫着
它们,不叹息
也不抱怨
在黑暗的苦役中站得笔直
在这里,伽蓝为人民发明了一个崭新的隐喻——被捶打的钉子,由此呈现了人民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在黑暗的苦役中站得笔直”。当然,人民的这种品质并非伽蓝第一次发现,但是伽蓝给出了一个新颖而简洁的表达。就像为一个数学表达式给出一种最简洁的证明,这表达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在艰难人世正直而有勇气地生活,是伽蓝笔下的人物普遍怀有的生活态度。《刷漆工的坚韧》中富有尊严感的刷漆工,《乡巴佬》中相信“还是干活更牢靠”(这几个字传达出了多少信息,其容量一点不亚于一行七言古诗,艺术上也不逊色于旧诗中最有名的句子)的乡巴佬,《这里》《暮年》中那些无名的打工者,《风沿着身体臃肿的弧线吹过来吹过去》中矿工出身的老诗人,都体现着这样的生活态度。这些人大多出身底层,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困于必死的棋局”,但他们并没有在与生活的斗争中垮下来,相反,他们在这一斗争中发展出一种倔强的也或是简单的信念,相信生命和生活的价值,更重要的,他们拥有一种从黑暗中发现甚至发明光的能力。前举《星空盖顶》中的抒情主人公处在一个“只剩下黑暗”的环境中,以至他自身“也变得漆黑”,然而他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现场还是发掘出了一座星空,一条翻卷的星河,从而填补了生命中“失去的部分”。另一首《春风不度》表现类似的主题:
钟情黑暗的草木
不去想黑暗以外的事情
在地下凝固的黑丝绒
有着失意者的倔强
冻土的萧疏张开万木
一颗星从天外投来
古老深情的一瞥
像死!化为心头的
物象,照彻寂静的木纹
哦,我是器皿,是建筑
是音乐挽住的清晨
冻土下,那些凝固的黑丝绒一样的草木之根似乎钟情、沉浸于黑暗,倾心死亡,然而它们却在黑暗中潜滋暗长,并终将在合适的时间张开万木。这是属于底层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在无边黑暗中,终有天外的星投来古老深情的一瞥,“化为心头的物象”。实际上,这天外的星就是心头的星,或者说,假若没有心头的星,你就看不见那天外的星。“像死!”,一个惊心动魄的比喻。为什么像死?因这远来的光像死一样坚定、权威,不可更改。也就是说,生和死一样不可更改。你说,还有比这对生更高的赞美吗?所以,这光能够“照彻寂静的木纹”,而让“我”感到自己是器皿,是建筑。器皿和建筑是人献给生的祭品。这深情一瞥的光照把“我”变成了器皿、建筑,变成了清晨,献给那个伟大的“生”——所谓“生生不息”,就依赖于这样一种献出。这种献出,在草木,就是“自然”,在人,却是一种赎救。因为长久以来,人在自利的驱动下,失去了献出的能力,所以人要重新向草木学习,赎还他的自然。
伽蓝宣称他的“个人美学”乃是“不高于/一株草木/亦不低于/一只鸣虫”(《个人美学》),而这样的生存乃使人成为“个体的君王”。我以为这是伽蓝通过他的诗向我们传达或者说重申了一种伟大的价值,一种宝贵的生命哲学。这种价值在冯至的十四行里(《尤加利树》《鼠曲草》),也得到了某种表达,但却没有达到伽蓝这样的强度,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完全。在冯至那里,一种时髦的集体理念驱逐了个体的意志,仿佛个体的意志是大人物的专利,而普通民众只有瞻仰膜拜的权利。而伽蓝说,我们是“个体的君王”,即便一株草木、一只鸣虫,也不妨碍其成为“个体的君王”。诗人这样说,真是太好了。那些在大人物眼中微渺的生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个人美学”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尊严。
需要注意的是,在伽蓝的“献出”和“个体的君王”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诗人所说的“献出”不是泯灭自我,陷入集体意志的泥淖;“个体的君王”也不是唯我主义,视自利为最高价值。“献出”而仍然是“个体的君王”,这样的献出才称得上宝贵;“个体的君王”而仍然勇于“献出”,这样的个体才配称“君王”。作为一种可贵的生命哲学,“献出”和“个体的君王”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我所经验的都被点亮了……”
也许因为伽蓝的这种生命哲学本源于植物的“存在”状态,所以它有一种强烈的趋光性。前述《星空盖顶》《春风不度》表现了处于黑暗环境中的生命对于光的信念和向往,另一些诗则表现了生命与光一刻也不能分开的款款深情。《早晨》一首表现了万物在晨光照耀下所呈现的熠熠光彩:
早晨到来。日光照耀梧桐树
金色梧桐
每一枝都是金枝
喜鹊在枝上喳喳叫
它的一半是金
另一半是喜悦
日光照耀山腰上的枣红马
慢慢走着
它的影子,一匹蓝马
在白墙上回头
……这一切,我所经验的
都被点亮了
多么好的时辰,多么短暂的永恒
蜻蜓般的翅子在唱
晨光下,“我所经验的/都被点亮了”,甚至连影子也有了色彩(注意,“一匹蓝马”)。真是无限美好的一刻。在这美好的时刻,一个深情的人定会想起爱人:“早晨到来,什么也不必说/我的心意你全都知道”。因为心中有爱,美好的变得加倍美好。这让我们想起海子的诗句:“晨光中……她看得我浑身美丽”。在诗人笔下,晨光是爱人,爱人也是晨光。我们读这首诗,也被晨光抚摸着,被爱人看着,也觉得浑身美丽了。在伽蓝笔下,黄昏的光芒则拥有另一种神圣的色彩:
一直围着金色的高塔颠簸
黄金砌成的高塔
世上最高的塔顶着雪
石头。经文。糟糕的晕眩
铁丝一样抽搐的风
心无杂念,只剩念诵的嘴唇
整整一生都会绕行这座塔
当太阳收尽鎏金
它悄无声息地矗存心灵
我肉体的旅行将是另一座
移行的高塔
光辉,轻盈,纤尘不染
这座黄金砌成的“世上最高的塔”,塔顶积雪,信徒们围绕它转经,念诵经文,仰望时阵阵晕眩。在黄昏的光照下,这黄金之塔光芒万丈。“黄金塔”虽然出自诗人的虚构,然而却真实地矗立在心灵的台基上。诗的结构严谨,丝丝入扣。第一节写远景。第二节写近景,并从塔转向人。第三节把外在的塔移置到心灵内部。最后一节人、塔合一,“我”的肉体就是一座“移行的塔”,“光辉,轻盈,纤尘不染”。诗人暗示我们,我们在人世的行路就是一场伟大的修行。显然,黄金塔的光芒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那里有另一个太阳为我们提供黄金的光芒。
要明白这黄金的光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需要联系诗人的另一首诗。在这首题为《汉语之光》的诗里,伽蓝写道:“每一个汉字就是一块方碑/……/要把自己写进汉语之美/借清风起笔,一个顿挫/就是一瓣沉思/一横一竖就能支撑/一个贫穷的屋顶/一撇一捺就重构一个/卑微的肉身……/让每一个汉字都闪闪发光、在最坚硬的黑暗中/搏动方正的心跳//万物将呼应它的光辉/万物将被永恒与青春所照耀”。对一个汉语诗人来说,最大的光源就是汉语。汉语就是早晨、中午和黄昏的太阳,诗人围绕这个太阳公转。诗人的道路,就是为汉语献出自己而迈上艰难行路。这个为汉语而修行的道路,骆一禾称为“修远”。而伽蓝恰好也写过一首叫“修远”的诗。这当然并非偶然。
在这一条诗歌的修行之路上,骆一禾强调人和诗的合一。在其杰作《修远》中,骆一禾说,“在朝霞里一个人变成一个诗人/诗人因自己的性格而化作灰烬/我的诗丢在了道路上/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修远呐/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人”。一个人被诗吸引,在语言中熔炼,变成一个诗人。这是一次脱胎换骨。很多诗人就止步于此。然而,对于骆一禾,这远远不够,他还要从诗人“变成一个人”。为此,他甚至不惜把诗丢在道路上。“变成一个人”当然不是回到起点的那个人,而是成为骆一禾所谓“博大生命”。这是一次更重要的脱胎换骨。在这一次的蜕变中,诗变成了熔炼生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和骆一禾一样,伽蓝也执着于诗与人的合一。他说,“诗人的属性与诗歌的属性,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诗人将写出什么样的诗歌。人即是诗歌本身”“伟大的诗人必须是诗与人的高度统一,不断统一,用尽整个生命与宇宙统一”。[7]伽蓝的诗之所以可靠,就是这个原因了。伽蓝还说,“真,即是诗的黄金,也是诗的灵魂。”[8]诗人所谓真,就是诗和人的统一性。伽蓝诗歌的根也就在他的“人”上,他的根所攥紧的“血块般的泥土”,也就是他自己身上的“人”。我们曾经说到,伽蓝的生活环境、生活阅历与其写作的紧密关系,但环境只是诗的土壤,并不是根。说白了,外部世界所以呈现诗意,是因为诗人心中有这个诗意,而这个诗意的根源则是诗人身上超乎常人的同情。诗从根本上说,依赖于、发端于这个同情。
“整体的诗意永远大于局部的诗意”
艾略特在一篇题为《什么是次要诗歌》的文章中曾经提出一个区分主要诗人和次要诗人的标准,就是考察其诗歌的整体是否大于部分之和。主要诗人的身上有一种整体性,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其整体建筑的一部分、一个部件,这些零散的部分和部件的全体构成了一座完整的诗歌大厦。单独就一个部分、一个部件来看,它们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没有它们,整个诗歌建筑的结构就会受到损害。次要诗人的作品彼此之间不存在这样一个结构关系,他们的每首诗仅仅作为单独的诗而存在,他们尽量让每首诗尽善尽美,而不是让整个诗歌建筑完美。一首诗一首诗看,次要诗人的作品是有竞争力的,甚至比主要诗人的作品更能满足心灵和审美的要求,但把它们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的时候,次要诗人的世界会因为缺乏整体性而垮塌,一首诗和另一首诗不能互相应和,这个部分和那个部分之间缺乏有机和内在的联系。在艾略特看来,造成这种无机性的原因主要是诗人结构意识和能力上的缺陷——一种理智和技艺的不足。然而,依我看,这种无机性还有更重要而内在的原因——诗人心灵上的缺陷。诗人的心灵力量不广、不大、不深,因而没有办法把他的精神贯穿到他所有的作品中去,这才是那种无机性的主要原因。伽蓝的诗,其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整体性,而这个整体性的来源就是他强悍的内在力量。当然,伽蓝拥有一种自觉的整体意识。他说:“整体的诗意永远大于局部的诗意。”[9]成为一个整体性的诗人,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他的。然而,我并不希望伽蓝因之产生那种跻身大诗人的野心。这样的野心并不会帮助诗人把诗写好,或者更有整体性,它只会把人引向某种夸饰的表演——这种表演我们在当代诗坛上已经见过很多了。它最坏的结果将导致心灵的坍缩和爱的能力的萎缩。我希望伽蓝继续壮大和丰富自己的心魂,成就骆一禾所说的辽阔胸怀,亲近这大地上的壮烈风景。这是一条艰难的道,然而也是唯一的道——正如伽蓝之前的写作已经证明了的,心灵的力量才是推动诗歌的黄金塔升向天穹的源源动力。
(2019年12月15日)
[1]扬·乌拉夫·于连.哦,现实:安娜·吕德斯泰德.诗歌中围绕一个母题中的编织物.// 在世上做安娜:安娜·吕德斯泰德诗选.杨蕾娜,罗多弼,万之,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81.
[2]参见西渡《多余的柔情——论从容的诗》,《诗探索》2018年第4辑。
[3]伽蓝《一个人的觉醒:创作自述》。
[4]伽蓝《一个人的觉醒:创作自述》。
[5]伽蓝《午夜》,见伽蓝自印诗集《加冕礼》(2019),第279页。
[6]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7]伽蓝《诗歌与人》。
[8]伽蓝《诗歌与人》。
[9]伽蓝《诗意的消解与事实的诗意》。
上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未尽之旅无尽之河》
西渡简介,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其间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2018年调入清华大学。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天使之箭》,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壮烈风景》《读诗记》等。
群山皱褶蕴藏永恒的生命肌里
——读伽蓝的诗
崖丽娟
恕我孤陋寡闻,在读到诗歌批评家、诗人西渡为伽蓝写的长篇评论《“荆棘林立着勃勃生机……”》之前,我对这位诗人一无所知。文中西渡先生也检讨自己:“伽蓝的诗让我大吃一惊。在这本诗集(指《加冕礼》)之前,我没有读过他的诗。刚开始,我多少带着一点挑剔甚至轻慢的态度”,细读之下,才“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诗人”,终于承认“读伽蓝的诗是我近几年最愉快的阅读经历之一,时时有发现的惊喜”。西渡先生的评价,让我不由郑重其事遍寻伽蓝的诗来阅读,然而,伽蓝公开发表的诗作并不是很多,恰好2020、2021年伽蓝接连出版了《加冕礼》《磨镜记》两本诗集,我才有幸得以集中细读品咂。
当今诗坛,不少诗人自我标榜,但真正得到读者认可的诗人并不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接地气,诗人隔绝于大众的生活,诗的经验与大众的经验互不相涉。而伽蓝的诗给人第一感觉就是很接地气。他长期作为一个普通小学教师生活在民间,默默地从少年写到了白头。伽蓝长于将生活中的物象和事态视作想象力的活水源头,在生活现场捕捉诗情,又善于从自己的阅历经验、灵魂深处提取最本真、最深情、最动人的东西,以高超的技艺进行诗性呈现与诗性反思,其笔力、思考力、思想魅力令人惊艳,厚实拙朴却闪耀着激情的光芒,彰显一种睿智和高远。如《遗言》:“怎么说呢,当阿喀琉斯结束这一世/而下一世将来之时/有什么话留给这世界吗/哪怕一粒沙,一阵最后的耳鸣/飘起来了,一朵云。他终于/什么也没说。只有一些/被苍蝇盯住的颠倒影像,在伤口中/颤抖,并将经历更深的战火”。透过诗人描绘的场景细节,读者不难体会到诗魂脉动的灵韵: “夜晚,来到一朵花上/一朵粉色露水/月亮在里面圆缺(《怀远》) ” ,仿佛被带入光风霁月之境,格外动人心扉。
伽蓝的诗机锋暗藏,直指人心。尽管诗与思都是对世界的洞见与照亮,但或许诗比单纯遵循逻辑规则的理性反思更适合认识事物的无限和绝对。伽蓝细腻的叙述、宽阔的视野、超拔的想象常能穿越意象细节进入对凡尘和俗世的反思警悟,其想象维度的开阔纵深极大拓展了诗意空间。他写《孤独》:“用半辈子反对无效。用十座三甲医院/治疗,无效。用最大剂量的欢乐/无效。没有什么痊愈它,包括爱/包括死。包括它本身。我们面对面坐着/一张桌子安静得像太平洋,晃了晃”。这些诗既是发现万物之美,也是探索人生奥义,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又如《多年以后》:“多年以后,生活里的人都不见了/发号指令的人与/唯命是从的人/而我还活着/在一本书中的躺椅上晒太阳/风吹着哗/歌唱的树叶/想念你们其中的一个/哦,年轻人,有空的话/也来这里坐坐/我们一起谈谈这时代的霉菌/有着难忘的气味和形色/一朵一朵在事物中间绽开/不想说话,就望一下/远处的山,最远的山上积着雪”。伽蓝将自己的情感情绪与真实的自然风俗、社会关系融为一体,将一己悲欢与众人悲欢、将土地厚重与天空高远连在一起,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份鲜活、厚重的生活档案,这些丰富的生活记忆将成为跨越时空的“活化石”为世人所珍爱。
伽蓝长期生活在北京门头沟山区。他的诗意探险就在雄浑辽阔的群山间展开,他把情感寄托于大地山川、日月流水、花草虫鸟。他的心灵是乡土的,气息是自然的,生命和爱情都与土地紧密地连在一起。他的诗充满了柔情,充满了生命活力,展示了大自然迷人的宁静与辽远:“渴了就喝山泉水。用核桃叶/弯成勺子/或直接趴在岩石上/摇荡的水草看起来很脏/水里小虫子在细沙上爬” “数数呼吸的绵羊,一会儿上了东坡/一会儿下西坡。数数雨后的草叶/草叶上滚动着露珠。露珠里的早晨/被鸟叫一粒一粒穿起来”。诗人构建的语境、形象,让原本粗狂的生活场景有了动人的景致,让朴实的日常多了凹凸深浅的回味。伽蓝发出的声音如此之美,透着温暖、善意,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审美境界,其调性和语感所产生的磁场让人清醒又震撼。这是伽蓝作为优秀诗人的独特魅力。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依我理解,“造境”“”是以意念与想象为境,““写境”是描写现实的景物。伽蓝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词,诗艺经过长期淬炼,无论“造境”还是“写境”都是高手。他的诗有对中国文化先贤和古典传统的深深敬意,如《哭梅》是借了《梅妃传》的典故,《石上吟》《微雨》等作品沾带古典诗歌的神韵;《春夜与吕二喝酒并谈起从前事》《王道士在终南山下遇太阳雨》《雪夜访朱耷》等从标题到境界都有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他把古典诗歌中的自然与人生情境进行现代重构,将古典精神揉入现实生活,这样的勾连萌发出现代新意,让越来越疏离、疲惫的心灵觅得一处宁静的精神栖所。伽蓝对古典诗歌是取其神而不囿于形式,如废名所言:诗的形式是散文化的,而这散文化的形式中须真有诗的内容。诗的内容充实了,必会找到恰当的形式以提升表现力。诗歌之所以放弃古典形式乃因其难以容纳这个时代复杂多样的内容。然而,诗歌的语言与形式获得了自由,并不意味着古典精神毫无价值。伽蓝在心灵深处接续古典的根脉,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却又根基于当下生活,在当下平凡生活里发现、提炼诗意并以独创的形式、形象表达出来,使古典被重新发现与诠释,并具有现代性。对于伽蓝,他日夜面对的群山皱褶里似乎蕴藏着气象万千、接通古今的艺术思想和美学原则,他又能以高超的技艺将之融会贯通于文本,彰显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生命肌理。这种贯通古典与现代的诗歌语言特征与作者的内在气质十分吻合,让他在当下众多类型化的诗人中鹤立鸡群。
伽蓝自述:“我经验有三种教育:一种是家乡的土地对我的教育,让我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一种从事教育工作时孩子对我的反哺,使我保持赤子之心。一种是诗的教育,引我发现自己,通过抒写感知生命的存在与完满。”下面这样的描述显然来自于家乡土地的教育:“盘旋在蓝色气流中/气体的鸥鸟平展翅翼/永远不能接近/鸣叫着,如此完美/与你同在/站在这里你如此完美/拥有一座固体与气体的大海/被安宁环绕着/被安宁搂在怀抱(《在椴木沟口远眺》)”透过这种源于经验的描述画面,读者不难体会诗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与无与伦比的热爱。诗人艾青说:“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 伽蓝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我认为这对诗人的创作思维是有影响的,孩子天真活泼,对世界充满新鲜的好奇,他们总是用积极的行动去探索未知,明朗的、动作性强的语句更易于孩子沟通交流,也许,这潜意识影响到伽蓝在诗中避免那些陈述或空泛的抒情却频频选择一些有独特情节、连续活动的场景,从而构成清晰的、易于想像的画面,如《小时候》写小马对于“成马”生活的猜测:“会长出翅膀飞越树林/在月下饮着冰水/有着吃不完的鲜草/每种草都有不同的香气/值得一生回味。”伽蓝语言的丰富性和美感,通过富于韵律的节奏,以天籁之音和自然之情启迪读者对于各种复杂事物的感悟与体验,这是非常难得的共情能力,令人深为叹服。那么,阅读与写作如何教育了作者呢?在《黄浦图书馆与博尔赫斯》这首诗中作者写的虽然是博尔赫斯的命运,但也不妨视作诗歌对诗人的教育: “失明的时刻,世界简化为一座/图书馆。古籍珍本环绕在身边/像哑掉的蝙蝠和蝴蝶明灭/而你只能用指纹、听力与嗅觉/辨认它们。模糊的话语森林/壁立的记忆旋转着悬崖/显露一种真实。试着继承这/崇高险峻的遗产,最精妙的部分/试着在灯火通明的黑暗中寻路/背过身,仍回到超重的微信时代/做理所应当的普通人。这已是最好答案/在黄浦图书馆,精神偶尔减轻了/物质的年轮,让人变得年轻/命运以绝伦的才华,在永恒的穹顶上/安装星辰,或者催促你/将心中的银河导入凝神的器官/你在松木桌边坐着,像年迈的神/食指敲击桌面:一个人在世上/行路,心仪的书就像候鸟/听从季节的召唤。而太阳巨大/正在 1920 年代的玻璃窗中沉璧/接下来,人类将进入阅读的时间……”诗歌如何写,写什么,选择什么语言来写,读完这首诗我们醍醐灌顶。
伽蓝诗歌语言具有很纯正的现代品质,语言简洁克制,非常理智地把语言组织成一种既能传达情感,又能精准表达这种情感的语言形式,如《山河还是旧山河》:“生活,去爱;然后忘掉生活,忘掉爱/这之间不会有痛苦了/花开着自己的花,叶子眨着自己的叶子/没有开始,也没有离别/一切归入语言的混沌,天地初长成”。不仅语言极富穿透力,而且情感冲击力特别强大,带来一种全然崭新的诗意。
伽蓝从1996年尝试写诗,2004年创作走上正轨,近二十年来对文字的痴迷,对诗艺的淬炼,正是他对生活的热烈拥抱和对生命的神圣叩问,他把有限的时光交付无限的文字升华为永无止境的艺术探索,我们相信穿越群山荆棘,伽蓝面前将展开奇迹般的美妙风景。
2022年1月20日

崖丽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研室主任、《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文艺报》《文学报》《上海文学》《作品》《百家评论》《南方文学》《广西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滇池》等发表诗歌和诗歌评论。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并有诗歌获奖。现居上海。

房子说:我打开所有的门和窗户,请风雪进来坐一坐。

崖丽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研室主任、《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文艺报》《文学报》《上海文学》《作品》《百家评论》《南方文学》《广西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滇池》等发表诗歌和诗歌评论。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并有诗歌获奖。现居上海。

伽蓝诗10首
---选自《磨镜记》
树枝摇曳
树枝摇曳,毛茸茸的鸟声
点缀清澈见底的绿意
涧底的琴声无人弹拨自己鸣响
终日不绝。山风徐徐吹过
而鸡犬并不相闻。抽完这枝烟
掐灭了烟头,忽然有着
躺在树尖上随风摇曳的冲动
在山腰上望一望,脚下的初夏
涌动,层层波浪此起彼伏
乡巴佬
的确,很多次
我都试着和自己谈
谈着谈着
就都忘掉了
还是干活更牢靠
可是干活时
又常常走神
不知道想什么
当周围的空气静下来
或一个雨点
啪地打在脸上
我又看见了山
温和地存在着
在它的存在里
我可有可无,但也
能感觉到它的温和
无处不在
不过,更多时候
我什么也不说
只是在树阴下
坐着,一根一根
抽着烟。天气很好
狭长的山谷里
不时响一声鸟叫
穿过慢慢
扩散的烟圈
一个瞬间
放下,放下……直到
放无可放,下无可下
终于可以一眼看穿了
转头,看窗口的吊兰
日子就这样过去
吊兰和吊额金睛猛虎
有什么分别?当我
铺开无声的宣纸
黑漆漆地游一回泳
拍打语言的浪花
有节奏地埋头,挥臂
游向空空的窗口
吊兰,长它的叶子
猛虎掏着瞎掉的耳朵
修远
——与子同袍
余音绕膝,对世事颇有悔意
湖水吞吐明月
蔷薇香透过熟睡的长安
骑马的人纷纷杀马取肉
从此,他们要靠一双脚掌
走掉剩下的黑
想象铺排的波纹,是
快刀归于长鞘,绮梦瘦成冬夜
怀疑论回到药片的偏头疼
在春天喝了一杯酒
到秋天才会大醉。读过的书
都妨碍花朵长成果实
写下的字只够安慰
自家的瓦上霜。想想从前
爱的种种可能
大多都成为不可能
这样也好
知道了,也就到了尽头
之后
母亲去世
让父亲和我都望见南山
杏花开着
雨雪飘来
中间隔着空荡荡的悲欢
小时候
跟着肥硕的臀走着
像一缕日光
穿过花阴。童年猜测着
成人的生活
会长出翅膀飞越树林
在月亮上饮下冰水
有着吃不完的鲜草
每种草都有不同的香气
值得一生回味。但它
不告诉你瞌睡
那穿透一切的引力
也不说出土地隐藏的秘密
每一条路都是一生的长度
山岗,一个单调的存在
好在背上没有鞍鞯
颈上没有绳索,在最初的时候
一头骡子
驾驭它的人
也是杀它的人
那人弯腰在地里干活
那人用袖子擦汗
那人埋头挖着秋天的金
为减少寻找
他把一匹年老的骡子
拴在一棵枯树上
然后,忘记了
秋天也忘记在下雨
洗着越来越薄的身板
骡子啃出一片圆形的
荒凉,饥饿与绝望
杀它的人躲在远处的屋檐下
吃一碗热汤面
他吃得很热闹
雨并没有停的迹象
玉米地喝水的声音
来自四面八方
对面山梁上的松树林
氤氲着一团
化不开的阴云
戏言
天上掉雹子
总会砸死一个秃子
老头子敲一声木鱼
全世界男人都要出家
只有半个男人
守着妻子
渡过黑夜茫茫
怀揣的雹子
化成了水
水升腾为云
下了更多雹子
一夜间,七十二僧还俗
娶了许多妻子
一夜间,三十六计
占领二十四城
一棵树拍巴掌
三个女人拍桌子
桌子漂在水上
三个女人三朵花
这些话说给猫听
猫伸个懒腰
变成老虎
骑着老虎去找你
你工作太忙
深夜还在写文件
一抬头就过了夏天
来不及说话
就要老了,来不及
黄昏就黎明
见面时
世界像一个钱包
钱币上的头像
换两杯咖啡
喝咖啡的人脸红
说,看什么看
没有时间和语言的压迫
窗户说:灵魂自由的国度,没有时间和语言的压迫。①
房子说:我打开所有的门和窗户,请风雪进来坐一坐。
火炉说:雪啊,你可以煮沸自己,沏一壶上好的碧螺春。
吉他说:我的六根清静,可以弹拨一曲浮世绘了,你尽管来听。
歌德说:我必须浮士德,非如此不歌德。
博尔赫斯说:把我的书放在火上烧吧,为我照亮这座图书馆。
戈麦说:对于我,诗歌是,一场空。②
椅子说:你们都坐下来,仔细听听这世上的沉默吧。
自注:①语出窗户诗《水仙》
②语出戈麦诗《那些是看不见的事物(给西渡)》
黄浦图书馆与博尔赫斯
失明的时刻,世界简化为一座
图书馆。古籍珍本环绕在身边
像哑掉的蝙蝠和蝴蝶明灭
而你只能用指纹、听力与嗅觉
辨认它们。模糊的话语森林
壁立的记忆旋转着悬崖
显露一种真实。试着继承这
崇高险峻的遗产,最精妙的部分
试着在灯火通明的黑暗中寻路
背过身,仍回到超重的微信时代
做理所应当的普通人。这已是最好答案
在黄浦图书馆,精神偶尔减轻了
物质的年轮,让人变得年轻
命运以绝伦的才华,在永恒的穹顶上
安装星辰,或者催促你
将心中的银河导入凝神的器官
你在松木桌边坐着,像年迈的神
食指敲击桌面:一个人在世上
行路,心仪的书就像候鸟
听从季节的召唤。而太阳巨大
正在二零年代的玻璃窗中沉璧
接下来,人类将进入阅读的时间……

伽蓝,北京市门头沟人。2004年开始诗歌写作,著有诗集《半夏之光》(2011年)《加冕礼》(2020年)《磨镜记》(2021年)。曾获“诗东西”青年诗人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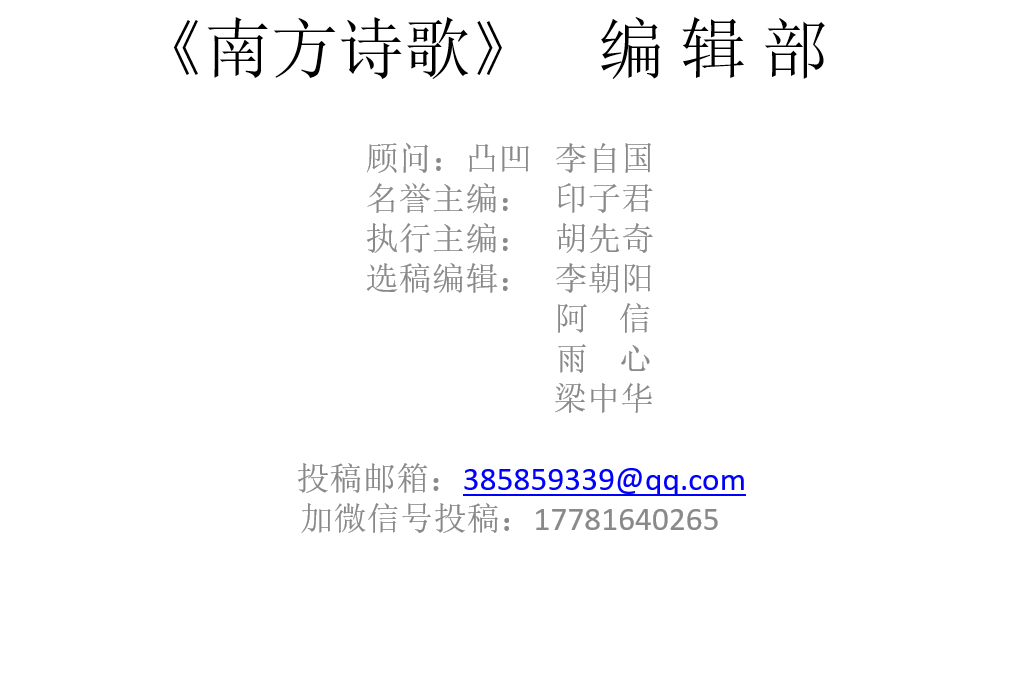
2021年《南方诗歌》总目录
2022年《南方诗歌》1月目录
“诗坛连理”:庭屹、哑石近作选
“诗坛连理”:谭毅、一行一家近作选
“张桃洲诗论”:存在的几副面孔
“张桃洲诗论”---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1990年代诗歌综论
”他山诗石“桑克:译诗9首
”他山诗石“:王家新最新译作选
”他山诗石“陈子弘:当代外国诗人十家
”他山诗石“汪剑钊译:俄罗斯黄金时代诗人关于冬天的诗
“珞珈诗派”黄斌:遁身于影像
”珞珈诗派“浅语纤云:液体的阳光流泻手心
“”珞珈诗派“陈O:我们生来是多么的白
“珞珈诗派”荣光启:唯有怀抱是盛装胜利的器皿
“珞珈诗派”孙雪:向星星借一双慧眼
”珞珈诗派“李金辉:在北方的大地上
“珞珈诗派”午言:边缘深陷于流动之美
“珞珈诗派”吴根友:让错过的美好如群星散落
“珞珈诗派‘夏雨:想像自己是一只狐狸
“珞珈诗派”钟立:那场错过的樱花雨
“珞珈诗派”水浅:我是你身后碎了一地的月亮
“珞珈诗派”刘焱红:大雪无声
"珞珈诗派“李浔:一只蚂蚁举着半片树叶向我走来
"珞珈诗派“上河:我们是永恒流动的肉体
”珞珈诗派“香香:面向春天 溺水或守口如瓶
霜扣儿:孤独的墓园
高鹏程:秋风赋
顔梅玖:看不见的风
张海宁:流进眼睛里的黑夜
蒲永见:永恒的雕像
龚学敏:把风箍得哭出声来
王江平:邀请一朵云来到我的屋中
高堂东溶:人性的波涛是打开一本更厚的词典
“崖丽娟诗访谈”海男:让诗的灵感从飞翔的想象力抵达现实
“90度诗点”:从历史中打开边塞--品读老房子,张媛媛
毛拾贰:那些苦难像是唇语结出的枳
李曙白:白色的沉默随波浪起伏
清平:两个人或许多人
伽蓝:与己书
徐敬亚:一粒雪就掩埋了冬天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好诗同读”:西渡、崖丽娟评伽蓝的诗》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中国大陆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免责申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举报收藏点赞
评论
(0条)

您需要登录后才能评论,点击此处进行登录。
登录后评论
最新资讯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华人头条-河南04-12 06:53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首部会长系列微剧《跟着会长看河南》开机大吉!
华人头条-河南04-03 22:39
預料「五一」黃金周800內地團訪港 多數留港2晚
华人头条-香港3小时前
合肥骆岗公园五一盛事连连!点燃你的假期沸点!
华人头条—安徽2分钟前
生活成本上涨,家庭选择兑现Kiwisaver减少食物开支
奇异新西兰5分钟前
下载华人头条

关于我们
© 2022 华人头条
服务热线 : 0591-83771172
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直播备案号 闽ILS备201708250005
举报热线:0591-83771172
举报邮箱:hrtt@52hrtt.com
免责声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