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高山流水:花 园 ∣ 唐寅九 、少况诗画唱和
2021-10-02 00:00 阅读量:7k+
华人号:南方诗歌
编者按:诗书画唱和,历来是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美事。在古人的诗画唱和中,常将诗题于画上,画家与诗人、书法家共同完成了美的创造。今天请大家欣赏唐寅九先生与少况的诗画唱和。本文原载于少况先生的微信公号“棱镜中”,感谢他的授权。
前言:
唐寅九
2021.9.12.
年代:2020

更大的漩涡

侧面的风
年代:2021

后院
年代:2021

紫竹院的早晨
年代:2021

下一步
材質:布面水泥、砂及水泥漆;尺寸:104*104cm;
年代:2021

异地次生林
材質:布面丙烯;尺寸:104*104cm;
年代:2021

佳县
年代:2019

璐城
年代: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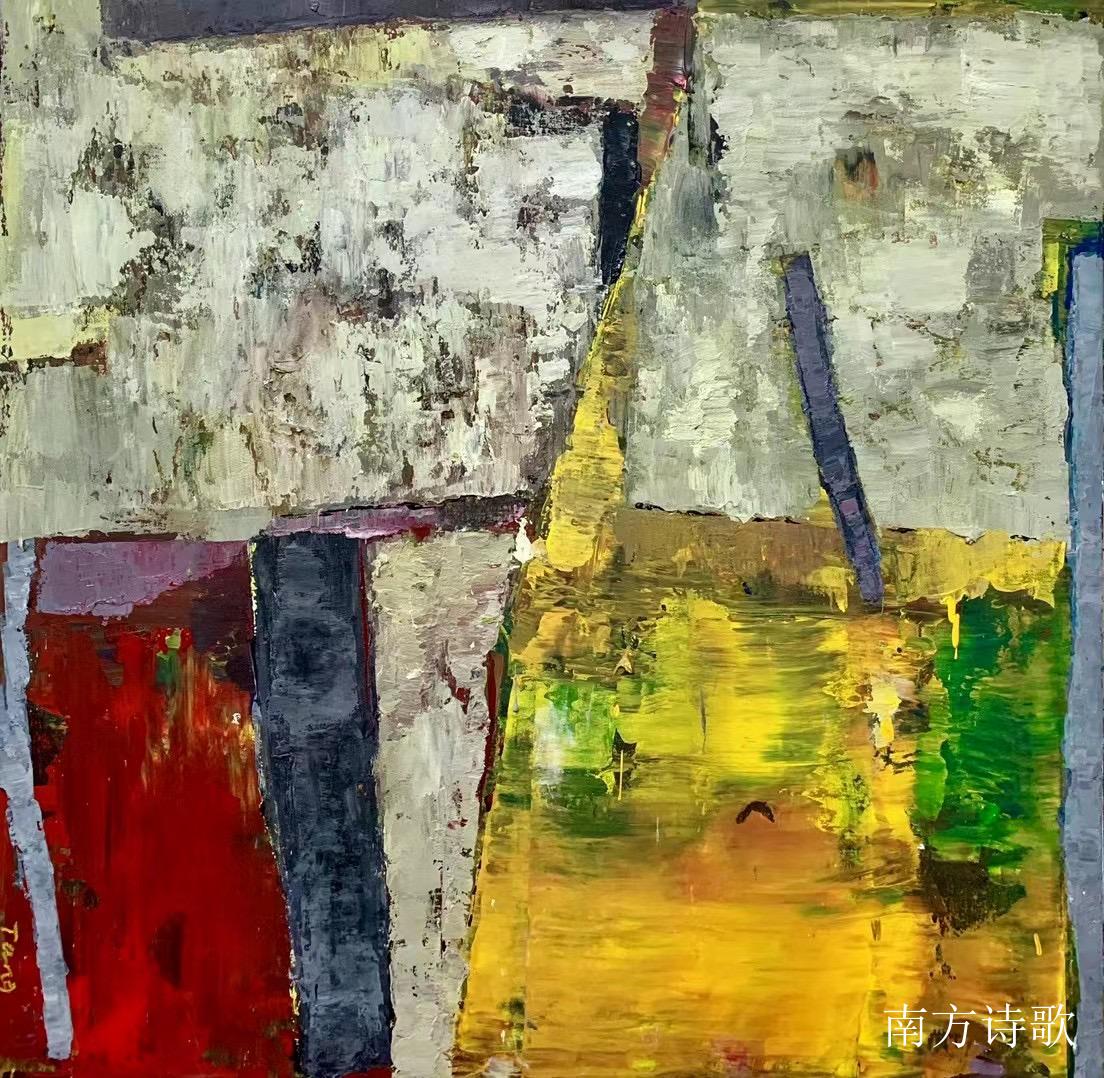
孟津
年代:2021

伊斯基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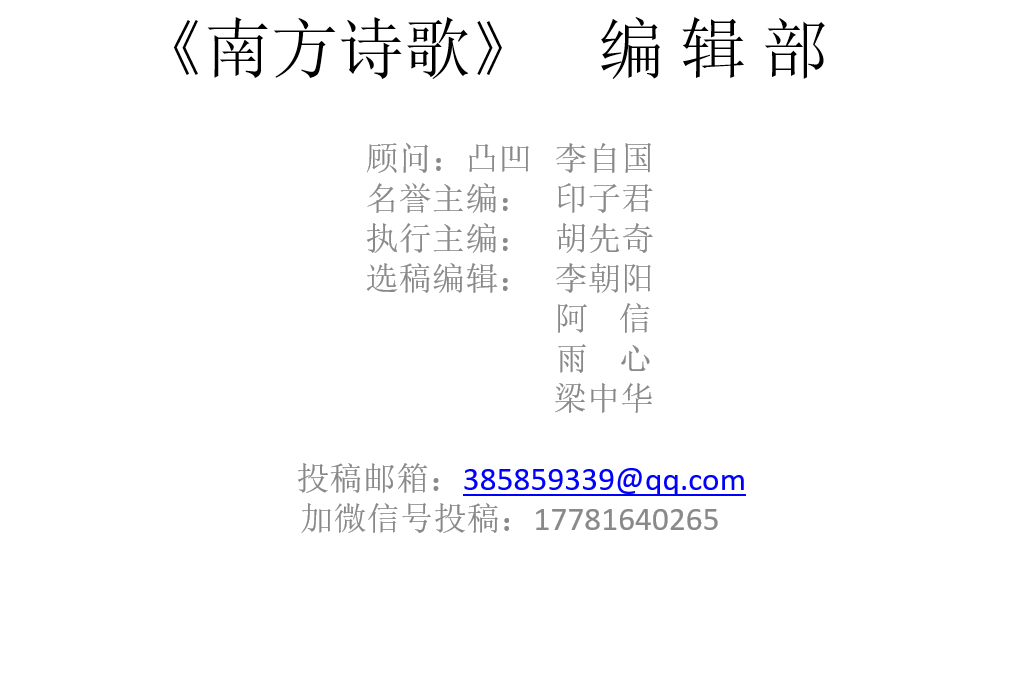
2021《南方诗歌》6月总目录
2021《南方诗歌》7月总目录
2021《南方诗歌》8月总目录
2021《南方诗歌》9月总目录
“新九叶”黄康益:委内瑞拉的阿维拉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分享《高山流水:花 园 ∣ 唐寅九 、少况诗画唱和》的全部内容,更多有关中国大陆华人最新消息、新闻,请多多关注华人头条频道。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APP,每天个性化推荐你想要看的华人资讯!
免责申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举报收藏点赞
评论
(0条)

您需要登录后才能评论,点击此处进行登录。
登录后评论
最新资讯
【战略合作邀约函】当下最佳合作契机来啦!
华人头条-河南07-31 22:22
2024“君品习酒·中国书院”文化活动在白鹿洞书院圆满收官
黔酒茶7小时前
茅台机场扎实做好航班换季消防安全保障工作
华人头条-贵州8小时前
孙含欣率队莅临艺立方参观交流
华人头条-贵州8小时前
民盟佛山市委赴黔东南开展“农村教育烛光行动”送教进校园活动暨考察调研
华人头条-贵州8小时前
下载华人头条

关于我们
© 2022 华人头条
服务热线 : 0591-83771172
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直播备案号 闽ILS备201708250005
举报热线:0591-83771172
举报邮箱:hrtt@52hrtt.com
免责声明
1、本站(网址:52hrtt.com)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等服务,用户保证对发布的内容享有著作权或已取得合法授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刊载的文章由平台用户所有权归属原作者,不代表同意原文章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3、因平台信息海量,无法杜绝所有侵权行为,如有侵权烦请联系我们(福建可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hrtt@52hrtt.com),以便及时删除。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
闽公网安备35010202000536号